
еҘӢ蹄зҷҪ马еҜә
жҖҺдёҚе–ҹеҸ№еӨ§иҮӘ然зҡ„й¬јж–§зҘһе·ҘпјҒеҘҪдёҖеә§еЁҒжӯҰйӣ„еЈ®зҡ„еұұеі°пјҢжӯЈйқўжңӣеҺ»пјҢжҒ°дјјдёҖдҪҚиә«зқҖй“ з”Ізҡ„жӯҰеЈ«пјҢжүӢжҢҒй•ҝеү‘пјҢеӨҙйЎ¶и“қеӨ©пјҢи„ҡиёҸж№ҹж°ҙпјҢиҝҷеӨ©е·ҘйҖ е°ұзҡ„еҮӣеҮӣеЁҒд»ӘпјҢд»Өжёёдәәй©»и¶іпјҢиӮғ然иө·ж•¬гҖӮ
иҝҷеұұеңЁи—Ҹж—ҸдҪӣ家жҷәиҖ…зңјйҮҢпјҢеҲҷзҠ¶иӢҘејәе·ҙпјҲжңӘжқҘпјүдҪӣпјҢжҳҜдёҖж–№йЈҺж°ҙе®қең°гҖӮе°ұеңЁиӨҡзәўиүІзҡ„еҲҖеҠҲиҝҮдјјзҡ„жӮ¬еҙ–дёҺеұұи„ҡжһ—жңЁиӢҚзҝ д№Ӣй—ҙпјҢжҳҺзҸ иҲ¬зҡ„镶еөҢзқҖдёҖеә§зҺІзҸ‘еү”йҖҸзҡ„еҜәеәҷпјҢеҲ«зңӢе®ғе°ҸпјҢеҚҙеЈ°еҗҚжҳҫиө«пјҢе®ғиҖҢеҖҚдҝ®е»әдәҺеҢ—йӯҸпјҢи·қд»Ҡе·Іжңү950еӨҡе№ҙзҡ„еҺҶеҸІпјҢжҳҜеҗҺејҳжңҹдҪӣж•ҷзҡ„еҸ‘зҘҘең°пјҢеӣ иҖҢеҖҚеҸ—иҶңжӢңгҖӮжҚ®иҜҙдёүдё–иҫҫиө–е–ҮеҳӣжӣҫеңЁжӯӨй©»й”ЎпјҢе…ӯдё–зҸӯзҰ…и·ҜиҝҮжӯӨең°ж—¶жӣҫдё“зЁӢеүҚеҫҖеҸ©еӨҙгҖӮзңҹеҸҜи°“еұұдёҚеңЁй«ҳпјҢжңүд»ҷеҲҷеҗҚгҖӮ
иҝҷе°ұжҳҜзҷҪ马еҜәпјҒдёҖдёӘиҝ·жј«зқҖйӯ…дәәзҡ„зҘһиҜқдј иҜҙпјҢж•ҷдәәзңӢдёҖзңјйЎҝз”ҹдёҮеҚғиҒ”жғізҡ„зҘһз§ҳең°ж–№гҖӮ
жҚ®иҜҙи®ёд№…д»ҘеүҚпјҢжңүй«ҳеғ§дә‘жёёиҮіжӯӨпјҢжүҖд№ҳзҷҪ马зҢқ然еҖ’жҜҷпјҢеғ§дәәе“ҖжҖңдёҚе·ІпјҢйҒӮ葬зҷҪ马并иҜөз»Ҹи¶…еәҰгҖӮеҝҪдёҖж—ҘпјҢзҷҪ马иҮӘз©әдёӯзҝ©з„¶иҖҢиҮіпјҢиҙҹй«ҳеғ§жңӣз©әиҖҢеҺ»пјҢз”ұжӯӨеҫ—еҗҚгҖӮдёҖиҜҙд»ҺеүҚж№ҹж°ҙжіӣж»ҘпјҢеІёиҫ№жқ‘еә„еҚҒйҒӯд№қж·№пјҢзҷҫ姓е“ҖжҖЁиҝһеӨ©пјҢдёҚе Әе…¶иӢҰгҖӮзӘҒ然д»Һеҙ–зјқдёӯдј жқҘзҷҪ马зҡ„еҳ¶йёЈпјҢжҙӘж¶ӣйҒӮжӯўгҖӮдё–дәәж„ҹжӮҹпјҢд№ғзӯ‘еҜәз„ҡйҰҷпјҢеҲ»зҷҪ马дәҺеҜәеЈҒпјҢжңқеӨ•зҘҲзҘ·гҖӮиҮӘжӯӨпјҢзҘӣйҡҫж¶ҲзҒҫпјҢж№ҹж°ҙзңҹзҡ„еңЁеұұи„ҡдёӢеӨ§еӨ§ең°з»•дәҶдёҖдёӘејҜпјҢиҝңзҰ»зҷҪ马жқ‘жөҒеҺ»гҖӮ
еҪ“然пјҢиҝҷжҳҜж°‘й—ҙдј иҜҙпјҢдёҚи¶ідёәдҝЎгҖӮдҪҶең°зҒөдәәжқ°пјҢжӣҫеҮ дҪ•еҜәдёӢдҪҸиҝҮдёҖдҪҚд»Өеә„жҲ·дәә家еҖјеҫ—йӘ„еӮІзҡ„дәәзү©гҖӮд»–е°ұжҳҜжң¬ж–Үи®°еҸҷзҡ„и—Ҹж—Ҹи‘—еҗҚж–ҮеҸІеӯҰ家й»Һе®—еҚҺпјҲеҚ“д»“·жүҺ然е§ҶеқҡжүҺи—Ҹ·иҙЎе·ҙжүҚи®©пјүе…Ҳз”ҹгҖӮ
дәәз”ҹиҪЁиҝ№пјҡд»Һзү§зҫҠеЁғеҲ°ж•ҷжҺҲ
1923е№ҙпјҲи—ҸеҺҶж°ҙзҢӘе№ҙи…ҠжңҲпјүй»Һе®—еҚҺеҮәз”ҹдәҺзҷҪ马еҜәдёңиҫ№еҮ еҚҒйҮҢзҡ„д№җйғҪеҚ—еұұдёҠдёҖдёӘжҷ®йҖҡеҶңзү§е®¶йҮҢпјҢе№је°Ҹзү§з«Ҙж—¶зҡ„д»–пјҢж•ҙеӨ©дёҖдјҡе„ҝи№Ұи№Ұи·іи·іжү‘жҚүиҚүдёӣдёӯзҡ„иҡӮиҡұпјҢдёҖдјҡе„ҝеҸҲжҺҸеҮәиҮӘеҲ¶зҡ„й№°з¬ӣпјҢеҗ‘зқҖи“қеӨ©зҷҪдә‘еҗ№еҘҸпјҢи¶ҙеңЁиҚүең°дёҠпјҢжү‘й—ӘзқҖд№Ңй»‘зҡ„еӨ§зңјзқӣпјҢд№…д№…ең°еҮқжңӣзқҖиҝңж–№……
“еұұйӮЈиҫ№жҳҜд»Җд№Ҳж ·еӯҗе‘ўпјҹ”
иҝҷдёӘй—®йўҳеңЁд»–еҝғйҮҢдёҚзҹҘйҮҚеӨҚдәҶеӨҡе°‘ж¬ЎгҖӮ
жҖӘдёҚеҫ—пјҢеұұйҮҢзҡ„еӯ©еӯҗпјҢйҷӨдәҶеӨ§еұұе’Ңиә«иҫ№зҡ„зҫҠзҫӨпјҢи§ҒиҝҮд»Җд№Ҳе‘ўпјҹ
иҰҒжҳҜиғҪдёҠеӯҰиҜҘжңүеӨҡеҘҪе•ҠгҖӮеҸҜжҳҜз©·д№Ўеғ»йҮҺпјҢиҝһдёӘеӯҰж ЎйғҪжІЎжңүгҖӮжІіеҜ№еІёзҡ„е°Ҹй•ҮдёҠиҷҪиҜҙжңүдёӘз§ҒеЎҫпјҢеҸҜйӮЈдёҚжҳҜдёҖиҲ¬дәә家зҡ„еӯ©еӯҗжүҖиғҪдёҠзҡ„иө·зҡ„гҖӮе·Із»Ҹ10еӨҡеІҒзҡ„е°ҸиҙЎе·ҙпјҢе°Ҫз®ЎеӨ©иө„иҒӘжҳҺеҚҙиҝҳжҳҜеӨ§еӯ—дёҚиҜҶдёҖдёӘгҖӮ
и—Ҹж—ҸжңүеҸҘи°ҡиҜӯпјҢж•ҙеӨ©и°Ӣз®—зҡ„пјҢжўҰйҮҢд№ҹеҫ—дёҚеҲ°пјӣжўҰдёҚеҲ°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йҶ’жқҘеҗҺеҚҙеҫ—еҲ°дәҶгҖӮжңүдёҖеӨ©ж”ҫзү§еҪ’жқҘпјҢйҳҝзҲёй«ҳе…ҙең°еҸ«д»–пјҡ“иҙЎе·ҙпјҢзһ§пјҢиҝҷжҳҜд»Җд№Ҳпјҹ”
“е•ҠпјҢжҳҜд№ҰеҢ…пјҒ”е°ҸиҙЎе·ҙеҒҡжўҰд№ҹжғідёҚеҲ°пјҢйҳҝзҲёдјҡзӘҒ然жғіеҲ°з»ҷд»–д№°дёӘд№ҰеҢ…гҖӮ
“иҝҷжҳҜзңҹзҡ„пјҹиҰҒйҖҒжҲ‘дёҠеӯҰж Ўпјҹ”
йҳҝзҲёиӮҜе®ҡең°зӮ№дәҶзӮ№еӨҙгҖӮ
“йҳҝзҲёпјҢжҲ‘иҰҒдёҠеӯҰдәҶпјҒжҲ‘иҰҒдёҠеӯҰдәҶпјҒ”е°ҸиҙЎе·ҙзҮ•еӯҗдјјеҫ—йЈһиҝҮеҺ»пјҢдёҖжҠҠжҠ“дҪҸйӮЈеҙӯж–°зҡ„д№ҰеҢ…пјҢжҠҠе®ғиҙҙеңЁи„ёдёҠпјҢ然еҗҺдёҖеӨҙжүҺиҝӣйҳҝзҲёзҡ„жҖҖйҮҢпјҢз”ңз”ңең°з¬‘дәҶгҖӮ
еҺҹжқҘпјҢд№қдё–зҸӯзҰ…жҙ»дҪӣдёәеҹ№е…»и’ҷи—ҸдәәжүҚпјҢеңЁзңҒеҹҺиҘҝе®Ғзӯүең°еҲӣеҠһи’ҷи—Ҹе°ҸеӯҰгҖӮе№ёиҝҗд№ӢзҘһдёҖеӨңд№Ӣй—ҙйҷҚеҲ°дәҶе°ҸиҙЎе·ҙиә«дёҠпјҢдҪҝд»–еҰӮж„ҝд»ҘеҒҝгҖӮ
д№ӢеҗҺпјҢд»–еҸҲжҠ•еҘ”еҲ°еҪ“е№ҙйқ’жө·и‘—еҗҚзҡ„и—Ҹж–ҮеҸІеӨ§еӯҰиҖ…пјҢж•ҷиӮІе®¶пјҢеӣҪж°‘е…ҡйқ’жө·ж”ҝеәңж•ҷиӮІеҺ…й•ҝпјҢи’ҷи—ҸеӯҰж Ўж Ўй•ҝ——зҪ—зғӯеқҡжҺӘеӨ§еёҲеӨ„з ”дҝ®и—Ҹж–ҮеҸІеӯҰгҖӮ1942е№ҙиҙЎе·ҙжүҚи®©д»ҘдјҳејӮзҡ„жҲҗз»©еңЁиҘҝе®Ғи’ҷи—ҸеӯҰж ЎжҜ•дёҡгҖӮе°ұиҒҢдәҺеӣҪж°‘е…ҡзҺүж ‘еҺҝж”ҝеәңпјҢ1949е№ҙжҳҘд»»зҺүж ‘ж—§ж”ҝеәңжңҖеҗҺдёҖд»»д»ЈзҗҶеҺҝй•ҝпјҢиҝҷе№ҙеӨҸеӨ©пјҢд»–еҰӮеҗҢеҫҖе№ҙдёәзјҙзәіж—§ж”ҝеәңзҡ„иҙЎзЁҺзүӣзҫҠпјҢеёҰзқҖеұһдёӢдёҖиЎҢжІҝи·Ҝж”ҫзү§зүӣзҫҠеҗ‘иҘҝе®ҒиҝӣеҸ‘пјҢйҖ”еҫ„йқ’жө·ж№–з•”ж—¶пјҢжңүж¶ҲжҒҜдј жқҘйқ’жө·и§Јж”ҫдәҶпјҒ25еІҒзҡ„д»–иҺ·жӮүиҝҷдёҖж¶ҲжҒҜпјҢеҮ еҲҶиҜ§ејӮеҮ еҲҶеҪ·еҫЁпјҢ然иҖҢпјҢдҪҝд»–е№ёиҝҗзҡ„жҳҜж—©е…ҲеҮ ж—ҘпјҢд»–е·Ід»Һеҗ„дёӘжё йҒ“жңүй—»д№Ӣе…ұдә§е…ҡи§Јж”ҫеҶӣи®ёеӨҡж„ҹдәәж•…дәӢпјҢжҒҚ然дёӯжҡ—дёӢеҶіеҝғ“жҲ‘иҰҒдёәж–°дёӯеӣҪеҒҡдәӣиҙЎзҢ®еҮәжҠҠеҠӣ”пјҢдәҺжҳҜд»–зқЈдҝғеұһдёӢжҠ“зҙ§ж—¶иҫ°пјҢиө¶еҫҖиҘҝе®ҒпјҢжңҖеҗҺжҠҠжүҖжңүзүӣзҫҠзјҙд»ҳдәҺеҪ“ж—¶зҡ„дёӯеӣҪдәәж°‘и§Јж”ҫеҶӣ第дёҖйҮҺжҲҳеҶӣпјҢеҪ“е№ҙзҡ„гҖҠи§Јж”ҫж—ҘжҠҘгҖӢ“и§Јж”ҫйқ’жө·”дёҖж–ҮеҲҠзҷ»дәҶиҝҷдёҖж¶ҲжҒҜпјҢеӣ иҖҢи§Јж”ҫйқ’жө·д№ӢзҘһеҸҲдёҖж¬Ўе…үйЎҫдәҶд»–гҖӮи§Јж”ҫеҶӣйҰ–й•ҝзңӢеҲ°иҝҷдёӘи—Ҹжұүе…јйҖҡгҖҒйЈҺеҚҺжӯЈиҢӮзҡ„и—Ҹж—Ҹдјҳз§Җйқ’е№ҙпјҢжҠҠд»–еҗёж”¶иҝӣдәҶйқ©е‘Ҫзҡ„йҳҹдјҚпјҢеҸҲдҝқйҖҒеҲ°иҘҝеҢ—дәәж°‘йқ©е‘ҪеӨ§еӯҰе…°е·һеҲҶж ЎпјҲиҘҝеҢ—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еүҚиә«пјүж·ұйҖ пјҢз»“дёҡеҗҺеҲҶй…ҚеҲ°з¬¬дёҖйҮҺжҲҳеҶӣеҸёд»ӨйғЁпјҢжҲҗдёәеҪӯеҫ·жҖҖйҰ–й•ҝзҡ„зҝ»иҜ‘гҖӮз”ұдәҺе·ҘдҪңеҮәиүІпјҢд»–еҫҲеҝ«иў«жҸҗеҚҮдёәз§ҳд№Ұ科й•ҝгҖӮиҙЎе·ҙжІҗжөҙеңЁе…ҡзҡ„йҳіе…үйӣЁйңІдёӢпјҢж·ұеҲҮж„ҹеҸ—еҲ°иҮӘе·ұзҡ„иө·жӯҘжҲҗй•ҝжҳҜе’Ңж–°дёӯеӣҪеҲҶдёҚејҖзҡ„пјҢзү№ең°з»ҷиҮӘе·ұиө·дәҶдёҖдёӘжұүеҗҚ——й»Һе®—еҚҺпјҢж„Ҹе–»ж–°дёӯеӣҪеғҸй»ҺжҳҺзҡ„жӣҷе…үз…§иҖҖеӨ§ең°пјҒд»–ж°ёиҝңеҝҳдёҚдәҶеҪӯиҖҒжҖ»зӯүйҰ–й•ҝеҜ№д»–зҡ„и°Ҷи°Ҷж•ҷеҜјпјҡеҘҪеҘҪе№ІпјҢе®—еҚҺеҗҢеҝ—пјҢжҲ‘们зҡ„дәӢдёҡпјҢйңҖиҰҒдёҖеӨ§жү№еғҸдҪ дёҖж ·зҡ„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дәәжүҚпјҒеҗҺжқҘд»–иў«и°ғе…Ҙи§Јж”ҫеҲқжңҹзҡ„дёӯе…ұиҘҝеҢ—еұҖе·ҘдҪңд»»жұӘеі°д№Ұи®°з§ҳд№ҰпјҢиҙҹиҙЈжұүи—Ҹзҝ»иҜ‘е·ҘдҪңгҖӮ
зҝ»иҜ‘жҳҜдёҖй—ЁжҜ”иҫғеӨҚжқӮзҡ„еӯҰй—®пјҢеҪ“ж—¶йҷҗдәҺжқЎд»¶пјҢзјәд№Ҹеҝ…иҰҒзҡ„иө„ж–ҷе’Ңе·Ҙе…·д№ҰпјҢжІЎжңүз»ҹдёҖзҡ„еҗҚиҜҚжңҜиҜӯгҖӮзҝ»иҜ‘йҰ–й•ҝи®ІиҜқе’ҢйҮҚиҰҒж–Ү件全йқ иҮӘе·ұзҡ„зҗҶи§Је’Ңи®°еҚ•иҜҚгҖӮд»–жҳҜдёӘжңүеҝғдәәпјҢе№іж—¶е°ҶиҮӘе·ұиҜ‘иҝҮзҡ„еҗҚиҜҚжңҜиҜӯйғҪйҖҗжқЎи®°еҪ•дёӢжқҘпјҢж—Ҙз§ҜжңҲзҙҜпјҢз«ҹжҳҜеҺҡеҺҡзҡ„дёҖжң¬гҖӮиҝҷжҳҜд»–ж•°е№ҙзҡ„еҝғиЎҖпјҢз»ҸиҝҮи®ӨзңҹзӯӣйҖүгҖҒж•ҙзҗҶгҖҒзј–зәӮдәҶж–°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Ҡзҡ„第дёҖйғЁгҖҠи—ҸжұүеӨ§иҫһе…ёгҖӢгҖӮиҝҷйғЁи‘—дҪңиў«еӣҪ家民委иӘүдёәе»әеӣҪеҲқжңҹ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ж°‘ж—Ҹж–ҮзҢ®д№ӢдёҖпјҢз»ҷдәҲе…ЁеҠӣж”ҜжҢҒпјҢдёҚжғңе·Ҙжң¬зҹіеҚ°еҮәзүҲпјҢдёәд»ҘеҗҺзҡ„зҝ»иҜ‘е·ҘдҪңеҸ‘жҢҘдәҶйҮҚеӨ§дҪңз”ЁпјҢд№ҹжҳҜд»–дёәж–°дёӯеӣҪеҘүзҢ®зҡ„第дёҖд»ҪеҺҡзӨјгҖӮ
继д№ӢпјҢиҘҝеҢ—еұҖж’Өй”Җд»–еҸҲиў«еҲҶй…ҚеҲ°еӣҪ家дёәеҹ№е…»еӨ§жү№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дәәжүҚзҡ„й«ҳзӯүйҷўж Ў——иҘҝеҢ—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гҖӮд»ҺжӯӨпјҢд»–иӮ©иҙҹиө·дәҶж•ҷд№ҰиӮІдәәзҡ„е…үиҚЈдҪҝе‘ҪгҖӮд»–ж—ўжңүжЎғжқҺиҠ¬иҠізҡ„ж¬Јж…°пјҢд№ҹжңүиҝҮдёҖжіўдёүжҠҳзҡ„еқҺеқ·пјҢдҪҶж— и®әеЈ°иӘүй№Ҡиө·иҝҳжҳҜиә«еӨ„йҖҶеўғпјҢд»–д»ҺжІЎеҝҳеҚҙиҮӘе·ұзҡ„дҪҝе‘ҪпјҡжңҹжңӣиғҪдёәиҝҷзүҮиӢҚеҮүиҖҢж·ұеҺҡзҡ„еңҹең°з•ҷдёӢзӮ№д»Җд№ҲпјҢиғҪдёәиҮӘе·ұеҸӨиҖҒзҡ„ж°‘ж—Ҹз•ҷдёӢзӮ№д»Җд№ҲгҖӮ
и·Ҝжј«жј«е…¶дҝ®иҝңе…®еҗҫе°ҶдёҠдёӢиҖҢжұӮзҙўпјҢйӮЈиҝҳжҳҜдёҠдё–зәӘдә”еҚҒе№ҙд»ЈеҲқпјҢд»–еңЁиҘҝеҢ—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иҜӯж–Үзі»д»»дё»д»»гҖӮз”ұдәҺд»–зҡ„еӯҰиҜҶе’ҢдёәдәәпјҢеңЁеҪ“ж—¶зҡ„еҗ„ж°‘ж—Ҹж•ҷиҒҢе‘ҳе·ҘдёӯйўҮжңүеҪұе“ҚпјҢжҳҜеҗ„ж°‘ж—Ҹж•ҷеёҲдёӯзҡ„дҪјдҪјиҖ…пјҢеҫҲеҸ—敬仰гҖӮеҪ“ж—¶пјҢеӣҪ家民委е’Ңй«ҳж•ҷйғЁж №жҚ®ж°‘ж—Ҹең°еҢәзҡ„е®һйҷ…пјҢиҰҒжұӮеҹ№е…»дёҖжү№еӯҰеҘҪж°‘ж—ҸиҜӯж–ҮгҖҒж°‘ж—ҸеҺҶеҸІе’Ңж°‘ж—ҸзҗҶи®әж”ҝзӯ–пјҢжҜ•дёҡеҗҺеҘ”иөҙж°‘ж—Ҹең°еҢәд»ҺдәӢж”ҝжқғе»әи®ҫе’Ңж°‘ж—Ҹж–ҮеҢ–гҖҒж•ҷиӮІдәӢдёҡдәәжүҚпјҢе…¶дёӯжңҖйҮҚиҰҒзҡ„дёҖйЎ№д»»еҠЎе°ұжҳҜиҰҒеҹ№е…»ж°‘ж—ҸиҜӯж–Ү——жұүиҜӯж–ҮдёӨз§ҚиҜӯж–Үзҡ„еҸЈиҜ‘е’Ң笔иҜ‘иғҪеҠӣгҖӮеӣ жӯӨпјҢзҝ»иҜ‘иҝҷй—ЁеӯҰ科жҳҜиҝҗз”ЁдёҖз§ҚиҜӯиЁҖжҠҠеҸҰдёҖз§ҚиҜӯиЁҖжүҖиЎЁиҫҫзҡ„дҝЎжҒҜеҶ…е®№йҮҚж–°е®Ңж•ҙиҖҢеҮҶзЎ®ең°иЎЁиҫҫеҮәжқҘпјҢиҰҒжұӮд»ҺиҜӯд№үгҖҒж–ҮдҪ“еҲ°иҜӯиЁҖйЈҺж јеңЁиҜ‘иҜӯдёӯеҫ—еҲ°жңҖиҙҙеҲҮгҖҒжңҖиҮӘ然зҡ„еҜ№зӯүиҜӯзҡ„еҶҚзҺ°пјҢйғҪж¶үеҸҠеҲ°иҜӯиЁҖзҗҶи®әе’Ңж–№жі•ж–№йқўзҡ„дёҖдәӣе…ұжҖ§й—®йўҳпјҢжүҖд»ҘпјҢиҒҶеҗ¬еҜјеёҲиҜҙзҝ»иҜ‘иҖ…еңЁеҜ№еҺҹж–Үзҡ„зҗҶи§ЈпјҢеҜ№еҺҹж–Үзҡ„ж•ҙдҪ“з»“жһ„е’ҢжҖқжғіеҶ…е®№жңүдёҖдёӘе…ЁйқўгҖҒеҮҶзЎ®зҡ„жҠҠжҸЎпјҢ然еҗҺиҰҒеҒҡеҲ°еӯ—ж–ҹеҸҘй…ҢпјҢз”ҡиҮіиҝһдёҖдёӘж ҮзӮ№з¬ҰеҸ·йғҪдёҚиғҪеҝҪи§ҶгҖӮиҝҷжҳҜйқһеёёйҮҚиҰҒзҡ„дёҖдёӘеӯҰд№ зҺҜиҠӮгҖӮиҝҷж—¶еҖҷзҡ„д»–е·Із»ҸиЎЁзҺ°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ж•ҷиӮІиҖ…зҡ„еҚ“и¶ҠжүҚиғҪпјҢеҪ“ж—¶д»–зҡ„еӯҰз”ҹ们е’ҢеҗҢдәӢ们еӣһеҝҶиҜҙ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жұүиҜӯзҡ„иҷҡиҜҚпјҢеңЁиЎЁиҫҫиҜӯд№үж–№йқўжңүзқҖеҚҒеҲҶеҫ®еҰҷзҡ„еҠҹиғҪпјҢеҚғдёҮдёҚеҸҜжҺүд»ҘиҪ»еҝғпјҢжҳҜжңәе·§зҡ„е…ій”®гҖӮд»–дёҫдҫӢиҜҙпјҡ“‘дҪ еқҗдёӢиҜҙ’”е’Ң‘дҪ еқҗзқҖиҜҙ’жүҖиЎЁиҫҫзҡ„ж„ҸжҖқеҹәжң¬зӣёеҗҢпјҢдҪҶиЎЁиҫҫзҡ„жғ…жҖҒеҚҙжҳҜдёҚдёҖж ·зҡ„гҖӮеүҚдёҖеҸҘеӯҗдёӯзҡ„‘дёӢ’жҳҜдёҖдёӘи¶Ӣеҗ‘еҠЁиҜҚпјҢиЎЁзӨәиҜҙиҜқиҖ…иҜ·еҜ№ж–№е…Ҳ‘еқҗ’еҗҺиҜҙпјӣиҖҢ‘зқҖ’еҲҷжҳҜдёҖдёӘж—¶жҖҒеҠ©иҜҚпјҢеұһиҷҡиҜҚзұ»пјҢйҷ„зқҖеңЁеҠЁиҜҚ‘еқҗ’зҡ„еҗҺйқўпјҢиЎЁзӨәиҜҙиҜқиҖ…иҰҒжұӮеҜ№ж–№еңЁ‘еқҗ’иҝҷдёӘиЎҢдёәжҢҒз»ӯзҡ„зҠ¶жҖҒдёӯиҜҙпјҢ‘еқҗзқҖ’жҲҗдёәеҜ№ж–№иҜҙиҜқзҡ„дёҖз§Қж–№ејҸпјҢдҪ“зҺ°дә’зӣёд№Ӣй—ҙзҡ„е№ізӯүе’ҢдәІиҝ‘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ңЁиҜ‘ж–ҮдёӯжҳҜеә”иҜҘеҢәеҲ«ејҖжқҘзҡ„”гҖӮ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и—Ҹж—ҸеӯҰиҖ…з«ҹ然еҜ№жұүиҜӯж–ҮжңүеҰӮжӯӨзІҫж·ұзҡ„з ”з©¶пјҢд»ӨеӨ§е®¶е•§е•§з§°зҫЎгҖӮ
жү§зқҖиҝҪжұӮпјҡд»–еҗ¬еҲ°дәҶж°‘ж—ҸжІүйҮҚзҡ„еҸ№жҒҜ
жңҲжңүйҳҙжҷҙеңҶзјәпјҢдәәжңүжӮІж¬ўзҰ»еҗҲгҖӮжҜҸдёҖдёӘеҗ‘дәӢдёҡе·…еі°ж”Җзҷ»зҡ„дәәпјҢеҫҖеҫҖе…ҚдёҚдәҶйҒӯеҸ—еқҺеқ·д№ӢиӢҰгҖӮжӯЈеҪ“д»–дёүеҚҒиҖҢз«ӢпјҢеӣӣеҚҒдёҚжғ‘д№Ӣе№ҙпјҢдёәзҘ–еӣҪеҮәеӨ§еҠӣпјҢе№ІдёҖз•ӘдәӢдёҡеғҸйј“ж»ЎйЈҺеёҶзҡ„иҲ№й©¶еҗ‘зҗҶжғіеҪјеІёд№Ӣйҷ…пјҢ“ж–Үйқ©”еғҸдёҖеңәйЈҺжҡҙпјҢе°Ҷд»–зҡ„жўҰеҮ»еҫ—зІүзўҺгҖӮд»–иў«жҲҙдёҠ“еҸҚеҠЁеӯҰжңҜжқғеЁҒ”пјҢ“й»‘её®йӘЁе№І”гҖҒ“иө°иө„жҙҫ”зӯүдёҖйЎ¶йЎ¶й«ҳеёҪеӯҗжёёж–—пјҢжҠ„家пјҢе…іиҝӣдәҶзүӣжЈҡгҖӮиҝһеҰ»еӯҗд№ҹдёҺд»–еҲ’жё…з•ҢйҷҗиҖҢзҰ»дәҶе©ҡгҖӮиӮүдҪ“е’ҢзІҫзҘһдёҠз»ҸеҸ—дәҶжңҖжғЁйҮҚзҡ„жү“еҮ»гҖӮдҪҶпјҢиҝҷдәӣд»–йғҪй»ҳй»ҳең°жҢәдҪҸдәҶгҖӮжңҖи®©дәәз—ӣжғңзҡ„жҳҜпјҢд»–зҸҚи—Ҹзҡ„д№ҰзұҚгҖҒиө„ж–ҷе’Ңи—ҸеӯҰз ”з©¶ж–ҮзЁҝпјҢеңЁиҝҷеңәжҙ»еҠЁдёӯйҒ—еӨұж®Ҷе°ҪгҖӮ
дҪҶд»–жІЎжңүеӣ жӯӨдёҖ蹶дёҚжҢҜпјҢеҸӘжҳҜе°ҶйӮЈйў—зҮғзғ§зҡ„зҒ«з§ҚжҡӮж—¶еҹӢеңЁеҝғеә•пјҢзӯүеҲ°дә‘ж•ЈйӣҫејҖпјҢйҳіе…үзҒҝзғӮзҡ„йӮЈдёҖеӨ©пјҢйҮҚж–°е°Ҷе®ғзҮғиө·пјҢз…§дә®иҮӘе·ұеүҚиҝӣзҡ„еҺҶзЁӢгҖӮ
дёғеҚҒе№ҙд»ЈеҗҺжңҹпјҢ“еӣӣдәәеё®”иў«зІүзўҺпјҢеҪ“е№ҙзҡ„иҘҝеҢ—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зҡ„иҖҒйўҶеҜјиҖҒеҗҢдәӢе’Ңз”ҳиӮғзңҒзҡ„йўҶеҜјд»¬еҮ з•ӘйӮҖиҜ·пјҢи®©д»–еҺ»д»»иҒҢдәҺиҘҝеҢ—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еүҜйҷўй•ҝпјҢеёҢжңӣд»–иғҪйҮҚиҝ”йҷўж Ўз»§з»ӯе·ҘдҪңпјҢжӢ…еҪ“жӣҙеҠ йҮҚиҰҒзҡ„и§’иүІпјҢеҸҜжҳҜиҝҷж—¶зҡ„д»–е·ІжҠҠиҮӘе·ұзҡ„жүҖжңүзІҫеҠӣдё“жіЁдәҺи—Ҹж—ҸеҺҶеҸІз ”究пјҢж•…иҖҢд»–е©үиЁҖи°ўз»қдәҶеҗ„дҪҚзҡ„зҫҺж„ҸпјҢжҜ…然еҶіз„¶зҡ„еҺ»дәҶйқ’жө·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пјҢйҰ–иҒҳдёәйқ’жө·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иҜӯиЁҖж–ҮеӯҰзі»зі»дё»д»»пјҢеҪ“ж—¶д»–зҡ„иҝҷдёӘзі»жңүи®ёеӨҡж•ҷеёҲжІЎжңүеҸ–еҫ—жӯЈејҸзҡ„ж•ҷеёҲиө„ж јпјҢе·ҘдҪңдёҠжңүи®ёеӨҡйҡҫд»Ҙе…ӢжңҚзҡ„еӣ°жғ‘е’Ңй—®йўҳпјҢжүҖд»ҘпјҢжңүи®ёеӨҡдәәжҖ»жҳҜиЎЁзҺ°зҡ„зј©жүӢзј©и„ҡпјҢдёҚж•ўеӨ§иғҶе·ҘдҪңгҖӮд»–зҹҘйҒ“еҗҺпјҢиҜӯйҮҚеҝғй•ҝең°еҜ№еӨ§е®¶иҜҙ“既然组з»Үи®©дҪ еңЁзі»йҮҢеҪ“иҖҒеёҲпјҢе°ұиҜҙз»„з»ҮжҳҜдҝЎд»»дҪ зҡ„пјҢжңүд»Җд№ҲдёҚж•ўеӨ§иғҶе·ҘдҪңзҡ„пјҹ”ж”ҫдёӢеҢ…иўұеҘҪеҘҪе·ҘдҪңпјҢз»„з»ҮжҳҜдҝЎд»»дҪ 们зҡ„пјҒ”
д»–иҝҳеёёеҲ°иҖҒеёҲ们зҡ„е®ҝиҲҚжҲ–иҜ·д»–们еҲ°д»–зҡ„жҲҝеӯҗйҮҢиҒҠеӨ©пјҲеҪ“ж—¶д»–дёҖдәәдҪҸеңЁеӯҰж ЎиҘҝеҚ—и§’зҡ„дёҖжҺ’еңҹе№іжҲҝзҡ„дёҖй—ҙжҲҝеӯҗйҮҢпјҢеҗғдҪҸеҚҒеҲҶз®ҖйҷӢпјҢдҪҶдёҚд»Ҙдёә然пјүдәҶи§Је®һйҷ…жғ…еҶөпјҢеӣ дёәи’ҷеҸӨиҜӯиЁҖж–ҮеӯҰдё“дёҡеҲҡеҲҡиө·жӯҘпјҢдёҚдҪҶж•ҷеёҲеҠӣйҮҸеҚҒеҲҶдёҚи¶іпјҢиҖҢдё”жІЎжңүзҺ°жҲҗзҡ„ж•ҷжқҗпјҢжңүеҮ й—ЁиҜҫзЁӢж— жі•ејҖи®ҫпјҢдёәдәҶдёҚиҖҪжҗҒеӯҰз”ҹзҡ„еӯҰд№ пјҢд»–еёҰйўҶеӨ§е®¶дё»еҠЁжүҝжӢ…дәҶгҖҠиҜӯиЁҖеӯҰжҰӮи®әгҖӢгҖҒгҖҠзҺ°д»Ји’ҷеҸӨиҜӯгҖӢгҖҒгҖҠзҝ»иҜ‘зҗҶи®әдёҺе®һи·өгҖӢгҖҒгҖҠеҸӨд»Ји’ҷеҸӨж—Ҹж–ҮеӯҰйҖүи®ІгҖӢзӯүеҮ й—Ёдё»иҰҒиҜҫзЁӢзҡ„и’ҷж–Үж•ҷжқҗзј–еҶҷе’Ңж•ҷеӯҰд»»еҠЎгҖӮиҝҷеҜ№дәҺеҪ“ж—¶зҡ„иҝҷдәӣдәәжқҘиҜҙпјҢе°Ҫз®Ўжңүж»Ўи…”зғӯжғ…пјҢдҪҶеңЁж—¶й—ҙе’ҢзІҫеҠӣдёҠжҳҜйҡҫд»ҘйҖӮеә”зҡ„пјҢйқўеҜ№еёҲиө„еҘҮзјәпјҢжңүдәӣиҖҒеёҲиә«дҪ“ж¬ дҪіиҝҷж ·зҡ„зҺ°е®һпјҢд»–дёҚиҫһиҫӣиӢҰжүҫжҜҸдёҖдҪҚиҖҒеёҲдҝғеҝғдәӨи°ҲеҒҡжҖқжғіе·ҘдҪңпјҢжғіе°ҪеҠһжі•и§ЈеҶій—®йўҳи°ғж•ҙж•ҷеӯҰи®ЎеҲ’пјҢжҠҠиҝҷеҮ й—ЁиҜҫеҲҶеҲ«е®үжҺ’еҲ°дёҚеҗҢеӯҰжңҹпјҢеҗҲзҸӯи®ІжҺҲпјҢй”ҷејҖж—¶й—ҙпјҢеҮҸиҪ»иҙҹжӢ…гҖӮе№¶ж— еҫ®дёҚиҮізҡ„е…іеҝғеұһдёӢз”ҹжҙ»пјҢе·ҘдҪңе’Ңиә«дҪ“пјҢе…ұеҗҢеҠӘеҠӣеәҰиҝҮйҡҫе…ігҖӮдҪҝиҖҒеёҲ们еҚҒеҲҶж„ҹеҠЁгҖҒжё©жҡ–е’ҢиҲ’еҝғгҖӮ
д»–еңЁж•ҷеӯҰе·ҘдҪңдёҠпјҢеҜ№дәәеҜ№е·ІйғҪеҚҒеҲҶиӢӣеҲ»пјҢдёҘж јж•ҷеӯҰзәӘеҫӢпјҢеҢ…жӢ¬иҮӘе·ұеңЁеҶ…йғҪиҰҒдёҘж јжү§иЎҢж•ҷеӯҰи®ЎеҲ’гҖӮиҜҫе Ӯж•ҷеӯҰдёҚеҫ—йҡҸж„Ҹи®ІжҺҲйӮЈдәӣдёҺж•ҷеӯҰеҶ…е®№ж— е…ізҡ„дёңиҘҝпјҢеёҰеҠЁдәҶеӨ§е®¶пјҢдҝқиҜҒж•ҷеӯҰзәӘеҫӢзҡ„дёҘиӮғжҖ§е’Ң规иҢғжҖ§гҖӮеңЁд»–еҪ“зі»дё»д»»йӮЈдәӣж—ҘеӯҗйҮҢпјҢиғҪз»ҸеёёеқҡжҢҒеҗ¬иҜҫпјҢеҸӮеҠ ж•ҷз ”е®Өеҗ„з§Қжҙ»еҠЁпјҢиҷҡеҝғеҗ¬еҸ–еӨ§е®¶ж„Ҹи§ҒпјҢдёә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иҜӯиЁҖж–ҮеӯҰзі»зҡ„ж•ҷеӯҰе»әи®ҫе’Ңйқ’е№ҙж•ҷеёҲзҡ„еҹ№е…»еҒҡеҮәдәҶд»Өдәәзһ©зӣ®зҡ„иҙЎзҢ®гҖӮжӯЈеӣ дёәеҰӮжӯӨпјҢзі»йҮҢзҡ„иҖҒеёҲдёҚи®әжҳҜе“ӘдёӘж°‘ж—Ҹзҡ„пјҢд№ҹдёҚи®әжҳҜиҖҒе№ҙж•ҷеёҲпјҢиҝҳжҳҜе№ҙиҪ»ж•ҷеёҲпјҢйғҪеҚҒеҲҶ敬йҮҚд»–гҖӮ
дёҚз•Ҹиү°йҡҫпјҡи°ӢеҲ’и—Ҹж–ҮеҸІеӯҰзҡ„жңӘжқҘ
дёҖж¬ЎеҺ»еҢ—дә¬ејҖдјҡпјҢд»ҺдёҖдҪҚеңЁдёӯеӨ®е·ҘдҪңзҡ„и—Ҹж—ҸйўҶеҜјйӮЈйҮҢеҗ¬еҲ°пјҢеӣҪйҷ…дёҠзҡ„и—Ҹж—Ҹз ”з©¶еӯҰжңҜдјҡи®®еңЁдёңдә¬еҸ¬ејҖпјҢз«ҹ然没жңүйӮҖиҜ·дёӯеӣҪзҡ„еӯҰиҖ…еҸӮеҠ пјҢ并且公然иҪ»и”‘ең°иҜҙпјҡи—ҸеӯҰиҷҪ然еңЁдёӯеӣҪпјҢдҪҶз ”з©¶и—ҸеӯҰеҚҙеңЁеӨ–еӣҪгҖӮиҝҷдёҖж–№йқўиҜҙжҳҺдәҶеӣҪеӨ–еӯҰжңҜз•ҢеҜ№жҲ‘еӣҪеӯҰиҖ…зҡ„иҪ»и§ҶпјҢеҗҢж—¶д№ҹеҸҚжҳ дәҶиҝҷж ·дёҖдёӘдәӢе®һпјҢз”ұдәҺеҺҶж¬Ўж”ҝжІ»иҝҗеҠЁпјҢи—ҸеӯҰз ”з©¶дёҖзӣҙдҪңдёәеӯҰжңҜзҰҒеҢәи®іиҺ«еҰӮж·ұпјҢеҲ«иҜҙжІЎжңүдёҖдёӘеғҸж ·зҡ„з ”з©¶жңәжһ„пјҢе°ұжҳҜд»ҺдәӢи—ҸеӯҰз ”з©¶зҡ„дәәд№ҹжҳҜеҜҘиӢҘжҷЁжҳҹпјҢж— жҖӘд№ҺжҲ‘们иҰҒеҸ—еҲ°жҙӢдәәзҡ„еҶ·еҳІзғӯи®ҪгҖӮ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и—Ҹж—ҸеӯҰиҖ…пјҢжҖҺиғҪдёҚж„ҹеҲ°з—ӣиӢҰе’ҢиҖ»иҫұе‘ўпјҒд»–жҶӢзқҖдёҖиӮЎеҠІпјҢеӣһжқҘеҗҺ马дёҠеҗ‘йҷўйўҶеҜјжұҮжҠҘгҖҒиҜ·зјЁпјҢеҶіеҝғжҲҗз«Ӣж°‘ж—Ҹз ”з©¶жүҖпјҢжҗһеҮәдёҖзӮ№еҗҚе Ӯи®©жҙӢдәәзһ§зһ§гҖӮд»–зҡ„иҰҒжұӮеҫ—еҲ°дәҶжңүе…ійўҶеҜјзҡ„еӨ§еҠӣж”ҜжҢҒпјҢеңЁдәәе‘ҳе°‘гҖҒз»Ҹиҙ№зјәгҖҒж•ҷеӯҰд»»еҠЎйҮҚзҡ„жғ…еҶөдёӢпјҢи®©д»–жҢ‘йҖүдәәе‘ҳпјҢжҢӨеҮәз»Ҹиҙ№пјҢдәҺ80е№ҙжҲҗз«ӢдәҶд»Ҙз ”з©¶и—ҸеӯҰдёәдё»зҡ„еӣҪеҶ…第дёҖ家民ж—Ҹз ”з©¶жүҖгҖӮдёҚд№…пјҢд»–иў«и°ғжҙҫеҲ°ж°‘ж—Ҹз ”з©¶жүҖд»»жүҖй•ҝгҖӮиҝҷдёӘжүҖжҳҜз»ҸзңҒ委гҖҒзңҒж”ҝеәңжү№еҮҶж–°жҲҗз«Ӣзҡ„зңҒеһЈе”ҜдёҖзҡ„з ”з©¶йқ’жө·ж°‘ж—ҸеҺҶеҸІгҖҒиҜӯиЁҖгҖҒж–ҮеҢ–гҖҒе®—ж•ҷе’Ңж°‘ж—ҸзҗҶи®әдёҺж°‘ж—Ҹж”ҝзӯ–зҡ„дё“й—Ёз ”з©¶жңәжһ„гҖӮдёҮдәӢејҖеӨҙйҡҫпјҢе°Ҫз®ЎдёҠзә§е’ҢеӯҰж ЎгҖҒе…ҡж”ҝйўҶеҜјйғҪеҚҒеҲҶйҮҚи§ҶиҝҷйЎ№дәӢдёҡпјҢдҪҶдёҖеҲҮйғҪжҳҜд»ҺеӨҙејҖе§ӢпјҢзү©иҙЁжқЎд»¶еҚҒеҲҶеҢ®д№ҸпјҢд№ҹж— з»ҸйӘҢеҸҜйүҙ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ңЁеӣ°йҡҫйқўеүҚд»–жІЎжңүзҠ№иұ«пјҢй«ҳе…ҙең°жҺҘеҸ—дәҶиҝҷдёӘд»»еҠЎпјҢеӣўз»“жүҖйҮҢзҡ„е…ЁдҪ“еҗҢеҝ—пјҢејҖе§ӢдәҶиү°йҡҫзҡ„еҲӣдёҡеҺҶзЁӢгҖӮд»–еёҰйўҶеӨ§е®¶е…ӢжңҚз ”з©¶дәәе‘ҳдёҘйҮҚдёҚи¶іпјҢж–ҮзҢ®иө„ж–ҷзүҮеӯ—ж— еӯҳпјҢеҠһе…¬жқЎд»¶еҚҒеҲҶз®ҖйҷӢпјҲеҪ“ж—¶д»–е’Ңе…¶д»–з ”з©¶ж•ҷеӯҰдәәе‘ҳеңЁдёҖй—ҙзӢӯе°Ҹзҡ„ж•ҷе®ӨйҮҢеҗҲзҪІеҠһе…¬пјүзӯүеӣ°йҡҫпјҢеҸ–еҫ—дәҶдёҖдёӘеҸҲдёҖдёӘжҳҫиө«зҡ„жҲҗз»©гҖӮеңЁд»–д»»иҒҢдёҚеҲ°дёүе№ҙзҡ„ж—¶й—ҙйҮҢпјҢе°ҶеҺҹжқҘзҡ„гҖҠйқ’жө·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гҖӢжҸҗеҚҮдёәеӯҰжңҜжҖ§еҲҠзү©——гҖҠйқ’жө·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еӯҰжҠҘгҖӢиҖҢеңЁеӣҪеҶ…еӨ–е…¬ејҖеҸ‘иЎҢпјҢ并е…ҲеҗҺжҲҗз«ӢдәҶ“ж°‘ж—ҸзҗҶи®әдёҺе®—ж•ҷз ”з©¶е®Ө”гҖҒ“ж°‘ж—ҸеҺҶеҸІз ”究е®Ө”“ж°‘ж—ҸиҜӯиЁҖж–ҮеӯҰз ”з©¶е®Ө”пјҢеҗҢж—¶пјҢз»„з»Үз ”з©¶дәәе‘ҳејҖе§Ӣж’°еҶҷгҖҠйқ’жө·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гҖӢиҝҷжң¬д№ҰзЁҝпјҢз§ҜжһҒз»„з»ҮдәәеҠӣжҗңйӣҶж°‘ж—Ҹж°‘дҝ—е’Ңж–ҮеҢ–еҺҶеҸІе®һзү©иө„ж–ҷпјҢдёәе»әз«Ӣ“ж°‘дҝ—з ”з©¶е®Ө”е’Ң“ж°‘ж—Ҹж°‘дҝ—ж–ҮеҢ–еұ•и§ҲйҰҶ”еҲӣйҖ жқЎд»¶гҖӮеңЁд»–дәІиҮӘдё»жҢҒдёӢпјҢеҺҶеҸІз ”究е®Өзҡ„еҗҢеҝ—们ејҖе§ӢдәҶиү°иҫӣзҡ„йқ’жө·ж°‘ж—ҸеҺҶеҸІиө„ж–ҷзҡ„жҗңйӣҶгҖҒзј–иҫ‘е·ҘдҪң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жңүеҮ дҪҚйқ’е№ҙз ”з©¶дәәе‘ҳпјҢд»ҺгҖҠжҳҺе®һеҪ•гҖӢгҖҒгҖҠжё…е®һеҪ•гҖӢзӯүз№ҒеӨҚзҡ„ж°‘ж—ҸеҺҶеҸІе…ёзұҚдёӯжҠ„еҪ•жңүе…ійқ’жө·еҗ„ж°‘ж—Ҹзҡ„еҺҶеҸІи®°иҝ°зүҮж®өпјҢжӣҙжҳҜдёҖйЎ№еҚҒеҲҶжһҜзҮҘиҖҢеҸҲдёәдәәжүҖйҡҫд»ҘдҪ“дјҡзҡ„иү°иӢҰе·ҘдҪңгҖӮдҪҶжҳҜпјҢ他们еқҡжҢҒдёӢжқҘдәҶпјҢе…ҲеҗҺеҚ°еҲ·жҲҗеҶҢзҡ„жңү6жң¬д№ӢеӨҡпјҢдёәеҗҺжқҘзҡ„з ”з©¶е·ҘдҪңеҸ‘жҢҘдәҶеҚҒеҲҶйҮҚиҰҒзҡ„дҪңз”ЁгҖӮиҝҷдёҖйғЁеҲҶиө„ж–ҷзі»еҲ—дёӣд№ҰпјҢеҗҺжқҘиў«дёӯеӨ®ж°‘ж—ҸеӨ§еӯҰжүҖйқ’зқҗпјҢж—Ҙжң¬еӨ§йҳӘ“ж°‘ж—ҸеӯҰеҚҡзү©йҰҶ”зӯүеӣҪеӨ–еӯҰжңҜжңәжһ„е’Ңж—Ҙжң¬гҖҒеҫ·еӣҪзӯүеӣҪеӨ–еӯҰиҖ…д№ҹиҝңйҒ“иҖҢжқҘиҙӯд№°дәҶзҷҫдҪҷеҶҢпјҢе…¶иө„ж–ҷд»·еҖјд№Ӣй«ҳе’ҢеҪұе“ҚеҠӣд№ӢеӨ§жҳҜеҪ“ж—¶жүҖжІЎжңүйў„ж–ҷеҲ°зҡ„гҖӮ然иҖҢпјҢд№қеҚҒе№ҙд»ЈдёӯеҗҺжңҹз•ҷеӯҳзҡ„йӮЈдёҖйғЁеҲҶз«ҹиў«еҪ“еҒҡ“еәҹзәё”еҚ–з»ҷдәҶеәҹе“Ғз«ҷпјҢжҲҗдёәйҡҫд»ҘжҢҪеӣһзҡ„йҒ—жҶҫпјҒ
и—Ҹж—ҸжңүеҸҘи°ҡиҜӯпјҢйӘҸ马й…ҚдёҠеҘҪйһҚжүҚжҳҫеҫ—зІҫзҘһгҖӮжҲҗз«Ӣйқ’жө·ж°‘ж—Ҹз ”з©¶жүҖпјҢжҒ°дјјеҰӮиҷҺж·»зҝјпјҢз„•еҸ‘дәҶд»–жһҒеӨ§зҡ„е·ҘдҪңзғӯжғ…гҖӮдёәдәҶжү©еӨ§и—ҸеӯҰз ”з©¶зҡ„еҪұе“ҚпјҢд»–еҸҲзүөеӨҙз»„з»ҮжҲҗдәҶи—ҸеӯҰз ”з©¶еӯҰдјҡпјҢеҮәд»»зҗҶдәӢй•ҝпјҢз»ҸеёёиҝӣиЎҢе№ҝжіӣзҡ„еӯҰжңҜдәӨжөҒдёҺжҺўи®ЁпјҢдёәи—ҸеӯҰз ”з©¶зҡ„е…ҙиө·е’ҢеҸ‘еұ•жҺЁжіўеҠ©жҫңпјҢеҗҺжқҘйқ’жө·ж°‘ж—Ҹз ”з©¶жүҖжҲҗдёәдәҶйқ’жө·з¬¬дёҖдёӘз”ұдёӯеӨ®ж°‘ж—ҸдәӢеҠЎе§”е‘ҳдјҡпјҢдёӯеӨ®ж•ҷиӮІйғЁжҢҮе®ҡдёәеҸҜжҺҲдәҲзЎ•еЈ«еӯҰдҪҚзҡ„еҚ•дҪҚпјҢд»–жң¬дәәжҲҗдёәдәҶйқ’жө·з¬¬дёҖдҪҚе”ҜдёҖеҸҜеёҰеҸҜжҺҲеӯҰдҪҚзҡ„ж•ҷжҺҲгҖӮ
йқ’жө·ж°‘ж—Ҹз ”з©¶жүҖеңЁд»–зҡ„йўҶеҜјдёӢпјҢд»ҘејәзғҲзҡ„ж°‘ж—ҸиҙЈд»»ж„ҹе’ҢзҘһеңЈзҡ„дҪҝе‘Ҫж„ҹпјҢз§ҜжһҒеұ•ејҖи—ҸеӯҰж–№йқўзҡ„з ”з©¶гҖӮ他们еңЁи—Ҹж—Ҹиө·жәҗгҖҒеҺҶеҸІеҸ‘еұ•гҖҒйҮҚиҰҒдәәзү©еҸҠе…¶ж”ҝжІ»гҖҒе®—ж•ҷгҖҒз»ҸжөҺзӯүйўҶеҹҹиҝӣиЎҢз ”з©¶пјҢз”ҡиҮіе°Ҷ笔и§Ұдјёеҗ‘жҹҗдәӣзҰҒеҢәпјҢиҝӣиЎҢжҺўзҙўпјҢеҸ–еҫ—дәҶеј•дәәзһ©зӣ®зҡ„жҲҗжһңгҖӮжҜ”еҰӮдј з»ҹзҡ„и§ӮзӮ№е°Ҷ“жң¬ж•ҷ”и§ҶдҪң“й»‘ж•ҷ”пјҢеҺҶеҸІдёҠжӣҫеҮ еәҰ“еӣҙеүҝ”гҖӮ他们з»ҸиҝҮд»”з»Ҷзҡ„еҲҶжһҗз ”з©¶и®Өдёәжң¬ж•ҷдҪңдёәи—Ҹж—ҸеҺҶеҸІдёҠзҡ„дёҖдёӘе®—ж•ҷпјҢеҜ№и—Ҹж—ҸзӨҫдјҡгҖҒж”ҝжІ»гҖҒеҺҶеҸІзҡ„еҸ‘еұ•пјҢеқҮиө·иҝҮдёҖе®ҡзҡ„з§ҜжһҒдҪңз”ЁпјҢжңүе…¶еҗҲзҗҶиҝӣжӯҘзҡ„дёҖйқўпјҢдёҚеә”е…ЁзӣҳеҗҰе®ҡгҖӮеҶҚеҰӮдёҖжҸҗи—Ҹж—ҸеҸІпјҢдј з»ҹзҡ„зңӢжі•е°ұжҳҜеҚ«и—ҸеҸІпјҢиҖҢеҝҪз•ҘдәҶе®үеӨҡең°еҢәгҖӮжңүзҡ„и—Ҹж—ҸеҸІзұҚд№ҹи®°иҪҪпјҡеҢ—ж–№йӣӘеҹҹд№ӢеўғеҚ«и—ҸдёӨең°пјҢж”ҝжІ»гҖҒе®—ж•ҷеӨҡж–№йқўж— дёҺеҢ№ж•ҢпјҢдәҰжҳҜж— еҸҜжҜ”жӢҹзҡ„жәҗең°гҖӮдёӯйғЁеә·еҢәпјҢж•ҷжҙҫдј—еӨҡпјҢж•ҷд№үз№ҒжқӮпјҢеҠҝеҠӣеҸҠиҙўеҜҢиҜёдёҡе…ҙж—әеҸ‘иҫҫгҖӮе®үеӨҡең°еҢәпјҢең°еҹҹдёҚе№ҝпјҢж”ҝж•ҷеӨҡж–№йқўи§„жЁЎдәҰе°ҸпјҢдёҺеүҚдёӨең°зӣёжҜ”пјҢдјјж— и®°иҪҪд№Ӣеҝ…иҰҒгҖӮдҪҶд»–и®ӨдёәпјҢеҚ«и—Ҹең°еҢәеңЁи—Ҹж—ҸеҸІдёҠзҡ„дё»дҪ“ең°дҪҚжҳҜж— еҸҜйқһи®®зҡ„пјҢдҪҶе®үеӨҡең°еҢәдҪңдёәж•ҙдёӘи—ҸеҢәдёҖйғЁеҲҶпјҢд№ҹжңүзқҖйҮҚиҰҒзҡ„еҪұе“Қе’ҢеҺҶеҸІең°дҪҚпјҢжңҖеҗҺдёҖдёӘи—ҸзҺӢжң—иҫҫзҺӣж¶ҲзҒӯдҪӣж•ҷеҘүз«Ӣжң¬ж•ҷеҗҺпјҢдҪӣж•ҷе°ұжҳҜз”ұе®үеӨҡжІіж№ҹд№Ӣең°зҡ„зҷҪ马еҜәдј дёҠеҺ»зҡ„гҖӮеҺҶеҸІдёҠжңүеҗҚзҡ„еҗҺејҳжңҹеҲӣе§ӢдәәжӢүй’ҰиҙЎе·ҙйҘ¶иөӣжҳҜе®үеӨҡдәәпјҢзҺ°иЎҢй»„ж•ҷеҲӣе§Ӣдәәе®—е–Җе·ҙпјҢд№ҹжҳҜе®үеӨҡдәә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е®үеӨҡд№ҹеҸҜз®—дҪңдҪӣеҸ‘жәҗең°д№ӢдёҖгҖӮе…¶д»–еңЁиҜёеҰӮжқҫиөһе№ІеёғгҖҒиөӨе°Ҡе…¬дё»зӯүзҡ„з”ҹеҚ’е№ҙд»ЈиҖғй—®йўҳдёҠпјҢд№ҹжңүдёҖдәӣдёҺдј з»ҹи§ӮзӮ№зӣёжӮ–зҡ„ж–°и®әзӮ№гҖӮиҝҷдәӣи®әиҝ°и§ӮзӮ№ж–°пјҢжұӮиҜҒе®һпјҢжӣҫеј•иө·и—ҸеӯҰз•Ңзҡ„йҮҚи§ҶпјҢ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з§ҚзғӯзғҲпјҢжҙ»и·ғж–°йІңзҡ„еӯҰжңҜж°”ж°ӣгҖӮе°ұжҳҜеӣҪеӨ–и—ҸеӯҰз ”з©¶жңәжһ„пјҢд№ҹйҖҗжёҗеҜ№д»–们зҡ„жҲҗе°ұйҮҚи§Ҷиө·жқҘгҖӮ
еҫ·й«ҳеӯҰеҜҢе ӘдёәдәәеёҲпјҢжЎғжқҺж»ЎеӨ©дёӢгҖӮд»–жңүзқҖе®Ҫйҳ”зҡ„еӯҰжңҜиғёжҖҖпјҢдёәдәҶж°‘ж—Ҹз ”з©¶дәӢдёҡпјҢд»–еңЁеј•иҝӣдәәжүҚгҖҒзҲұжҠӨдәәжүҚе’Ңеҹ№е…»дәәжүҚж–№йқўд№ҹдҪңдәҶеӨ§йҮҸзҡ„е·ҘдҪңгҖӮеңЁеӯҰж ЎйўҶеҜјзҡ„ж”ҜжҢҒдёӢпјҢд»–еҗёеј•е’Ңеӣўз»“еҗ„ж°‘ж—Ҹзҡ„еӯҰжңүдё“й•ҝзҡ„дәәжүҚпјҢдҪҝж°‘ж—Ҹз ”з©¶жүҖдәәжүҚиҚҹиҗғпјҢдёәе…¶еҸ‘еұ•еҘ е®ҡдәҶеқҡе®һзҡ„еҹәзЎҖгҖӮдҫӢеҰӮпјҡж°‘ж—ҸеӯҰж•ҷ欧жҪ®жіүпјҲдҫ—ж—ҸпјүгҖҒж°‘ж—ҸиҜӯиЁҖеӯҰ家жқҺе…ӢйғҒпјҲеңҹж—ҸпјүгҖҒйҹ©е»әдёҡпјҲж’’жӢүж—ҸпјүпјҢж°‘ж—Ҹж°‘дҝ—еӯҰ家зҺӢж ‘дёӯпјҲи’ҷеҸӨж—ҸпјүгҖҒеҺҶеҸІеӯҰ家е®ӢиҝҒз”ҹпјҲжұүж—Ҹпјүж°‘ж—ҸзҗҶи®ә专家еӯ”иҜҰеҪ•пјҲеӣһж—ҸпјүгҖҒйҷҲе…үеӣҪпјҲжұүж—Ҹпјүзӯүж•ҷжҺҲпјҢйғҪжҳҜеҪ“ж—¶еңЁзңҒеҶ…еӨ–йўҮжңүеҪұе“Қзҡ„еӯҰиҖ…пјҢ他们дёәж°‘ж—Ҹз ”з©¶жүҖзҡ„еҘ еҹәе’ҢеҸ‘еұ•еҒҡеҮәдәҶйҮҚиҰҒзҡ„иҙЎзҢ®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е№ҙиҪ»зҡ„еӯҰиҖ…пјҢд№ҹеңЁд»–зҡ„йўҶеҜје’Ңе…іеҝғдёӢиҝӣжӯҘеҫҲеҝ«пјҢд»ҠеӨ©пјҢйғҪжҲҗдёәжҲ‘зңҒеӯҰжңҜз•Ңзҡ„дҪјдҪјиҖ…гҖӮдҫӢеҰӮжҳҹе…ЁжҲҗж•ҷжҺҲпјҲеңҹж—ҸпјүгҖҒйҷҲжҹҸиҗҚж•ҷжҺҲпјҲи—Ҹж—ҸпјүпјҢе·Із»ҸжҳҜй©°еҗҚзңҒеһЈзҡ„и—ҸеӯҰ家гҖҒеҺҶеҸІеӯҰ家пјӣи’ҷеҸӨж—ҸеҺҶеҸІеӯҰ家йҹ©е®ҳеҚҙеҠ еңЁеӣҪеҶ…и’ҷеҸӨж—ҸеҺҶеҸІеӯҰз•Ңд№ҹжҳҜйўҮжңүеҪұе“Қзҡ„еӯҰиҖ…дәҶпјҢзӯүзӯүгҖӮ他们зҡ„жҲҗй•ҝдёҺд»–еҪ“еҲқеңЁж°‘ж—Ҹз ”з©¶жүҖйҮҢиҗҘйҖ иүҜеҘҪзҡ„еӯҰжңҜж°ӣеӣҙпјҢе…іеҝғе’Ңж”ҜжҢҒ他们зҡ„з ”з©¶е·ҘдҪңжҳҜеҲҶдёҚејҖзҡ„гҖӮ
жҪңеҝғеӢҫз”»пјҡ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зҡ„иЎҚеҸҳиҪЁиҝ№
и—Ҹж—ҸжңүеҸҘи°ҡиҜӯпјҡдёҚдәҶи§Је…ҲзҘ–еҺҶеҸІзҡ„дәәпјҢеҘҪдјјжңӘй•ҝе°ҫе·ҙзҡ„зҢҙе„ҝгҖӮи—Ҹж—ҸпјҢ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еҸӨиҖҒзҡ„ж°‘ж—ҸпјҢжңүеҮ еҚғе№ҙзҡ„ж–ҮжҳҺеҸІгҖӮеҸҜд»ҘиҜҙиҮӘд»ҺжңүдёӯеҚҺж°‘ж—Ҹзҡ„еҺҶеҸІпјҢд№ҹе°ұжңүи—Ҹж—Ҹзҡ„еҺҶеҸІгҖӮжңүе…іиҝҷдёӘж°‘ж—Ҹзҡ„дј иҜҙе’ҢеҸ‘еұ•пјҢж—©е°ұи§ҒиҜёдәҺеҸӨд»ЈеҸІзұҚд№ӢдёӯгҖӮе…ідәҺд»–зҡ„ж—ҸжәҗпјҢдј—иҜҙзә·зәӯгҖӮжңүжәҗдәҺеҚ°еәҰд№ӢиҜҙпјҢжәҗдәҺ马жқҘеҚҠеІӣд№ӢиҜҙпјҢжәҗдәҺзј…з”ёд№ӢиҜҙпјҢжәҗдәҺйІңеҚ‘иҜҙпјҢжәҗдәҺиҘҝзҫҢиҜҙпјҢжұүи—ҸеҗҢжәҗиҜҙпјҢзӯүзӯүпјӣйўҮеӨҡжҖҘиҜҠпјҢиҺ«иЎ·дёҖжҳҜгҖӮ
然иҖҢд»–еҸҰиҫҹи№Ҡеҫ„пјҢд»Ҙи—Ҹж—Ҹзҡ„дёҖдёӘйғЁеҲҶ——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дҪңдёәз ”з©¶еҜ№иұЎпјҢз»ҸиҝҮеӨҡе№ҙзҡ„з ”з©¶е’ҢиҖғиҜҒпјҢд»ҘеӨ§йҮҸдәӢе®һдёәдҪҗиҜҒпјҢжҸҗеҮәдәҶи—Ҹж—ҸжәҗдәҺйқ’и—Ҹй«ҳеҺҹиҝңеҸӨеңҹи‘—еұ…ж°‘зҡ„ж–°и§ӮзӮ№пјҢд»ҺдёҖдёӘдҫ§йқўеҗ‘еӨ§е®¶еұ•зӨәеҮәи—Ҹж—ҸжёҠжәҗеҸҠе…¶еҸ‘еұ•иҝҮзЁӢпјҢи®©дәәиҖізӣ®дёҖж–°гҖӮ
з”ұдәҺең°еҹҹиҫҪйҳ”е’Ңй•ҝжңҹзҡ„жј”еҸҳеҸҠе…¶д№ жғҜе’ҢиҜӯиЁҖе·®ејӮпјҢи—Ҹж—Ҹең°еҢәдёҖиҲ¬еҲҶдёәдёүеӨ§ең°еҢәпјҢеҚіи—Ҹж—ҸеҸІд№ҰжүҖз§°дёҠйҳҝйҮҢдёүеӣҙгҖҒдёӯеҚ«и—ҸеӣӣеҰӮгҖҒдёӢжңөеә·е…ӯеІ—гҖӮе…¶дёӯжңөеә·пјҲеҸҲз§°жңөз”ҳжҖқжҲ–жңөз”ҳпјүеҸҲеҲҶдёәжңөе ҶгҖҒжңөйәҰдёӨйғЁеҲҶгҖӮжңөйәҰеҚіе®үеӨҡгҖӮжүҖи°“е®үеӨҡпјҢжҚ®иҜҙпјҢз”ұеңЈең°еҚ°еәҰйҮ‘еҲҡеә§еҢ—иө°дёҖзҷҫз”ұз”ёпјҢжңүиҗЁиҝҰеӨ§еҜәпјҢеҸҲеҗ‘еҢ—иө°дёҖзҷҫз”ұз”ёпјҢеҚіжӯҘе…ҘжңөйәҰи—ҸеҢәгҖӮе®ғи¶ҠиҝҮй•ҝжұҹдёҠжёёзҡ„е·ҙйўңе–ҖжӢүеұұпјҢдёңеҚ—жңүйҳҝжІҒеІ—ж—Ҙе’ҢеӨҡжӢүи®©жҜӣдёӨеә§еұұпјҢеҸ–дёӨеұұеҗҚйҰ–еӯ—еҗҲ并иҖҢз§°“е®үеӨҡ”гҖӮиҝҷдёҖең°еҢәпјҢжҳҜжҲ‘еӣҪи—ҸеҢәдёӯжһҒдёәйҮҚиҰҒ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гҖӮдёҖжҳҜең°еҹҹиҫҪйҳ”пјҢеҢ…жӢ¬д»Ҡеӣӣе·қиҘҝеҢ—йғЁгҖҒз”ҳиӮғеҚ—йғЁгҖҒжІіиҘҝиө°е»ҠеҸҠйқ’жө·е…ЁйғЁи—ҸеҢәпјҢзәҰ100дёҮе№іж–№е…¬йҮҢе’Ңиҝ‘200дёҮдәәеҸЈпјӣдәҢжҳҜе®ғжҳҜи—Ҹдј дҪӣж•ҷж јйІҒжҙҫе®—еёҲе®—е–Җе·ҙзҡ„иҜһз”ҹең°пјҢеҸҲжҳҜ第еҚҒеӣӣдё–иҫҫиө–е–ҮеҳӣгҖҒ第еҚҒеёҲзҸӯзҰ…еӨ§еёҲзҡ„иҜһз”ҹең°пјҢеңЁж”ҝжІ»дёҠеҜ№ж•ҙдёӘи—ҸеҢәеҪұе“ҚиҫғеӨ§пјӣдёүжҳҜе®ғдёҖзӣҙеӨ„еңЁе’Ңжұүж—Ҹең°еҢәжҺҘеЈӨең°еёҰпјҢеңЁй•ҝжңҹзҡ„дәӨжөҒдёӯдёҚиғҪдёҚеҸ—еҲ°жұүж—Ҹе’Ңе…¶д»–ж°‘ж—Ҹ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ёҖйғЁ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еҸ‘еұ•зҡ„еҺҶеҸІпјҢд№ҹжҳҜдёҖйғЁиў–зҸҚзҡ„и—Ҹж°‘ж—ҸеҸ‘еұ•еҸІгҖӮйҖҸиҝҮ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еҸ‘еұ•еҸІпјҢд»ҺдёӯеҸҜд»ҘзңӢеҲ°ж•ҙдёӘи—Ҹж—ҸеҺҶеҸІеҸ‘еұ•зҡ„з«ҜеҖӘпјҢиҝҷгҖӮдёҚиғҪдёҚиҜҙжҳҜеҜ№еҸІеӯҰз•Ңзҡ„дёҖдёӘйҮҚеӨ§иҙЎзҢ®гҖӮ
дёәзІҫеҝғеӢҫз”»еҮә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иЎҚеҸҳзҡ„еҺҶеҸІиҪЁиҝ№пјҢд»–еҮ д№ҺиҠұиҙ№дәҶеҚҠз”ҹзҡ„еҝғиЎҖгҖӮж—©еңЁ1950е№ҙпјҢд»–е°ұжңүиҝҷж–№йқўзҡ„жһ„жғіпјҢз»Ҳеӣ е®ўи§ӮжқЎд»¶жүҖйҷҗиҖҢжңӘиғҪйҒӮж„ҝгҖӮеңЁиҘҝеҢ—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ж—©жңҹд»»ж•ҷжңҹй—ҙпјҢд»–жӣҫдёәзј–еҶҷеӨ§еӯҰж•ҷжқҗпјҢж·ұе…Ҙи—ҸеҢәжҗңйӣҶж•ҙзҗҶиў«ж№®жІЎдәҶзҡ„дјҳз§Җж–ҮеҢ–йҒ—дә§пјҢдёҖеҺ»е°ұжҳҜеҚҠе№ҙпјҢеңЁжө©еҰӮзғҹжө·зҡ„е…ёзұҚдёӯиӢҰиӢҰеҜ»и§…зқҖпјҢжңҹжңӣзқҖпјҢеёҢжңӣиғҪеӨҹжңүжүҖеҸ‘зҺ°……еҠҹеӨ«дёҚиҙҹжңүеҝғдәәпјҢд»–еұ…然еңЁеӨҸжІідёҖеұұеҢәе°ҸеҜәеҲҷеҲҷеҜәеҸ‘зҺ°дәҶеӨұдј еӨҡе№ҙзҡ„и—ҸеӯҰйҮҚиҰҒж–ҮзҢ®гҖҠе®үеӨҡж”ҝж•ҷеҸІгҖӢпјҢеҰӮиҺ·иҮіе®қпјҢеҚғж–№зҷҫи®ЎеҖҹеҲ°еӯҰж ЎпјҢз»„з»Үж•ҷеёҲеңЁдёҖдёӘжңҲзҡ„ж—¶йҷҗйҮҢпјҢзЎ¬жҳҜдёҖдёӘеӯ—дёҖдёӘеӯ—ең°жҠҠиҝҷйғЁиҝ‘зҷҫдёҮеӯ—зҡ„жө©зҖҡе·ЁеҚ·жү“еҚ°дәҶеҮәжқҘпјҢиЈ…и®ўдәҶдә”еҚҒеҶҢпјҢ并з«ӢеҚізқҖжүӢиҝӣиЎҢзҝ»иҜ‘пјҢеҲ—е…ҘеӣҪ家йҮҚзӮ№еҮәзүҲи®ЎеҲ’гҖӮгҖҠе…үжҳҺж—ҘжҠҘгҖӢжӣҫзҷ»иҪҪдәҶиҝҷж–№йқўзҡ„ж¶ҲжҒҜпјҢеҗҺеӣ “еҸҚеҸі”ж–—дәүејҖе§ӢиҖҢиў«жқҹд№Ӣй«ҳйҳҒпјҢзӣҙеҲ°зІүзўҺеӣӣдәәеё®еҗҺпјҢжүҚз”ұз”ҳиӮғдәәж°‘еҮәзүҲзӨҫеҮәзүҲдәҶпјҢе…¶и“қжң¬е°ұжҳҜд»–жңҖеҲқжү“еҚ°зҡ„50еҶҢзҡ„дёҖйғЁеҲҶгҖӮиҝҷйғЁи‘—дҪңзҡ„еҸ‘зҺ°дёҺеҮәзүҲпјҢеңЁи—ҸеӯҰз•ҢйғҪеҸ‘з”ҹдәҶйҮҚеӨ§зҡ„еҪұе“ҚгҖӮ
дёәз§ҜзҙҜиҜҰеӨҮзҡ„иө„ж–ҷпјҢд»–еҹӢеӨҙдјҸжЎҲз»ҸеёёжҳҜйҖҡе®өиҫҫж—ҰгҖӮжңүж—¶дёәдәҶж ёеҜ№дёҖдёӘй—®йўҳпјҢжҹҘйҳ…иө„ж–ҷзӣҙж·ұеӨңпјҢз”ҡиҮідёҚзҹҘдёҚи§үдёӯдјҸжЎҲиҖҢзң гҖӮжңүж—¶жҖқиҖғй—®йўҳиҝӣе…ҘеҝҳжҲ‘зҡ„еўғз•ҢпјҢеёёеёёеҝҳдәҶеҗғйҘӯгҖӮеҪ“д»–жҜҸжүҫеҲ°дёҖд»ҪйңҖиҰҒзҡ„иө„ж–ҷж—¶пјҢеёёеёёй«ҳе…ҙеҫ—жүӢиҲһи¶іи№ҲпјҢжҠҠиҝҷеҪ“еҒҡеәҹеҜқеҝҳйЈҹжңҖеҘҪзҡ„иЎҘеҒҝгҖӮд»–жӣҫиө°и®ҝдәҶи®ёеӨҡеҜәйҷўе’ҢеёҗзҜ·пјҢеғ§дҫЈе’Ңзү§ж°‘пјҢжҲҗдёәд»–зҡ„жңӢеҸӢгҖӮд»ҺзҫӨдј—дёӯеҗёеҺ»иҗҘе…»пјҢе·ІжҲҗдёәд»–йҮҚиҰҒзҡ„зҹҘиҜҶжәҗжіүгҖӮйҖҡиҝҮеӨ§йҮҸзҡ„з§ҜзҙҜе’ҢжҪңеҝғз ”з©¶пјҢеҮ еҚҒе№ҙеҰӮдёҖж—ҘпјҢд»–иҺ·еҫ—дәҶзҙҜзҙҜзЎ•жһңгҖӮе…ҲеҗҺеңЁеӯҰжңҜеҲҠзү©дёҠеҸ‘иЎЁдәҶж•°д»ҘеҮ еҚҒзҜҮзҡ„дјҳз§ҖдҪңе“ҒпјҢе°Өе…¶д»ҘгҖҠйқ’жө·ең°еҗҚиҖғгҖӢгҖҒгҖҠи®әеҚ“д»“и—Ҹж—Ҹзҡ„еҺҶеҸІеҸҠж–ҮеҢ–зү№еҫҒгҖӢгҖҒгҖҠеҚ“д»“и—Ҹж—Ҹзҡ„еҺҶеҸІгҖӢгҖҒгҖҠиҘҝзҫҢеӨҡеә·и—Ҹж—ҸгҖӢгҖҒгҖҠи—Ҹж—Ҹз ”з©¶дёӯйңҖиҰҒжҫ„жё…зҡ„еҮ дёӘй—®йўҳгҖӢгҖҒиҜ‘и‘—гҖҠеӣҪйҷ…дё»д№үе’Ңж°‘ж—Ҹдё»д№үгҖӢгҖҒгҖҠжұүи—Ҹи’ҷеҺҶеҸІиҝ°з•ҘгҖӢгҖҠи®әеҚ“д»“и’ҷеҸӨж—Ҹзҡ„еҺҶеҸІеҸҠж–ҮеҢ–зү№еҫҒгҖӢгҖҒгҖҠ“иҘҝзҫҢ”дёҺеӨҡеә·и’ҷеҸӨж—ҸгҖӢгҖҒгҖҠе…ідәҺи—Ҹж—ҸеҺҶеҸІж–ҮеҢ–зҡ„继жүҝеҸ‘еұ•й—®йўҳгҖӢзӯүи®әж–ҮйғҪжҳҜйўҮжңүеҪұе“Қзҡ„йҮҚиҰҒи®әи‘—пјҢд»ЈиЎЁдәҶд»–дёҖз”ҹз ”дҝ®и—ҸеӯҰзҡ„ж ёеҝғжҖқжғіе’ҢдёӯеҝғеҶ…е®№пјҢд»Һеҗ„дёӘдёҚеҗҢи§’еәҰе’Ңдҫ§йқўеҜ№е®үеӨҡзҡ„и—Ҹж—ҸеҸІдҪңдәҶи®әиҝ°гҖӮиҝҷдәӣж–Үз« зҡ„зү№зӮ№жҳҜи§ӮзӮ№ж–°гҖҒи®әиҝ°ж·ұгҖҒиө„ж–ҷиҜҰе®һпјҢе…·жңүиҫғејәзҡ„иҜҙжңҚеҠӣгҖӮжӯӨеӨ–пјҢеҘ№иҝҳдё»жҢҒзј–иҜ‘дәҶгҖҠе®үеӨҡж”ҝж•ҷеҸІгҖӢгҖҠйҳҝиҠ’зҸӯжҷәиҫҫгҖӢзӯүжңүеҪұе“Қзҡ„и—ҸеӯҰи‘—дҪңгҖӮиҝҷдәӣи‘—иҝ°дёәд»–еҗҺжқҘзј–еҶҷеҮәзүҲе®Ңж•ҙзҡ„гҖҠ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еҸІгҖӢеҘ е®ҡдәҶеҹәзЎҖгҖӮд»–еҜ№еҫ…е·ҘдҪңдёҖдёқдёҚиӢҹпјҢеӨ„еӨ„д»Ҙиә«дҪңеҲҷпјҢеҜ№еҫ…еҗҢеҝ—ејҖиҜҡеёғе…¬пјҢе…іеҝғзҲұжҠӨдёӢзә§е’ҢеҗҢдәӢпјӣиҖҢдё”еңЁеӯҰжңҜз ”з©¶дёҠд№ҹжҳҜеӯңеӯңд»ҘжұӮпјҢеӢӨеҘӢеҲ»иӢҰпјҢеӯҰйЈҺдёҘи°ЁпјҢе ӘдёәиЎЁзҺҮпјӣд»–е–„дәҺ“зҝҳзҝҳй”ҷи–ӘпјҢиЁҖеҲҲе…¶жҘҡ”пјҢдёҚйҡҸжіўйҖҗжөҒпјҢе…¶жҲҗжһңиңҡеЈ°жҲ‘зңҒд№ғиҮіеӣҪеҶ…еӨ–еӯҰжңҜз•ҢпјҢзңҹжңү“еҰӮеҪұд№ӢйҡҸеҪўпјҢе“Қд№Ӣеә”еЈ°”зҡ„еҪұе“ҚеҠӣгҖӮ1993е№ҙ10жңҲ2ж—ҘпјҢдёҖйғЁеҲҶеңЁиҘҝе®Ғе·ҘдҪңзҡ„1959е№ҙеүҚеҗҺжҜ•дёҡзҡ„еҺҹиҘҝеҢ—ж°‘ж—ҸеӯҰйҷўиҜӯж–Үзі»зҡ„еӯҰз”ҹ们专门дёәеәҶиҙәд»–е…ӯеҚҒеӨ§еҜҝпјҢж¬ўиҒҡдёҖе ӮиҝҪеҝҶеёҲжҒ©гҖӮеӯҰз”ҹ们еңЁз»ҷд»–зҡ„иҙәдҝЎдёӯпјҢеӯ—йҮҢиЎҢй—ҙж— дёҚжҙӢжәўзқҖеҜ№д»–зҡ„зңҹжҢҡ敬зҲұд№Ӣжғ…гҖӮ他们еңЁиҙәдҝЎдёӯеҶҷйҒ“пјҡ“敬зҲұзҡ„й»ҺиҖҒеёҲпјҢеҠҹеҠіеҶҢдёҠиҷҪ然没жңүеҶҷдёҠжӮЁзҡ„еҗҚеӯ—пјҢдҪҶжӮЁзҡ„еҗҚеӯ—ж°ёиҝңй“ӯи®°еңЁжҲ‘们зҡ„еҝғдёӯпјҢжӮЁиҫӣеӢӨзҡ„жұ—ж°ҙе·Із»ҸеҢ–дёәдәүеҰҚеҗҗиҠізҡ„иҠұжңөпјҢејҖж”ҫеңЁзҘ–еӣҪзҡ„иҘҝеҢ—еӨ§ең°пјҢйӮЈжңөжңөйІңиүізҡ„иҠұжңөпјҢдёҚе°ұжҳҜжӮЁзҡ„еҝғиЎҖе’Ңз»“жҷ¶еҗ—пјҒ”жғ…зңҹж„ҸеҲҮгҖҒжңҙе®һиҖҢе…¬е…Ғзҡ„иҜ„д»·гҖӮ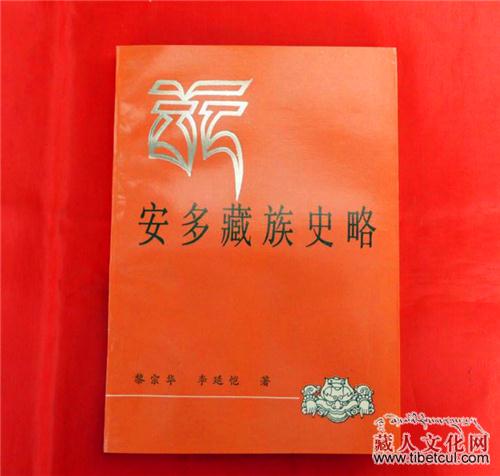
з»ҸиҝҮй•ҝжңҹзҡ„еҮҶеӨҮе’ҢеҠӘеҠӣпјҢеҮқз»“зқҖд»–еҚҠз”ҹеҝғиЎҖзҡ„гҖҠ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еҸІз•ҘгҖӢпјҢ1992е№ҙз”ұйқ’жө·дәәж°‘еҮәзүҲзӨҫеҮәзүҲдәҶгҖӮиҝҷйғЁд№ҰдёҖй—®дё–пјҢе°ұеңЁи—ҸеӯҰз•Ңеј•иө·еҫҲеӨ§йңҮеҠЁгҖӮиҝҷжҳҜдёҖйғЁжҜ”иҫғе®Ңж•ҙзҡ„ең°еҹҹжҖ§и—Ҹж—ҸеҸІгҖӮе®ғзі»з»ҹең°и®әиҝ°дәҶ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зҡ„жәҗжөҒеҸҠе…¶ж”ҝжІ»гҖҒз»ҸжөҺгҖҒж–ҮеҢ–гҖҒеҺҶеҸІзӯүзҡ„еҪўжҲҗе’ҢеҸ‘еұ•гҖӮеңЁи®әиҝ°и—Ҹж—Ҹзҡ„жёҠжәҗж—¶пјҢдёҚжҳҜз®ҖеҚ•ең°еҜ№иҜёеӨҡеӯҰиҜҙдәҲд»ҘеҗҰе®ҡпјҢиҖҢжҳҜйҖҸиҝҮеӨ§йҮҸеҸІе®һпјҢзү№еҲ«жҳҜеә”з”ЁиҖғеҸӨеҸ‘зҺ°гҖҒж–Үзү©еҮәеңҹеҸҠ其科еӯҰжөӢе®ҡж•°жҚ®пјҢиҮӘ然иҖҢд»ӨдәәдҝЎжңҚең°е°ҶиҮӘе·ұзҡ„и§ӮзӮ№е…¬иҜёдәҺдј—пјҢеҚі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иө·жәҗдәҺеҸӨд»Јйқ’жө·й«ҳеҺҹзҡ„еңҹи‘—еұ…ж°‘пјҢ并еңЁй•ҝжңҹзҡ„еҸ‘еұ•иҝҮзЁӢдёӯжҸүиҝӣжІіж№ҹең°еҢәе…¶д»–е°‘ж•°ж°‘ж—Ҹе…ұеҗҢеҸ‘еұ•дёәеҪ“д»Ҡ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гҖӮ
еңЁиҝҷйғЁд№ҰдёӯпјҢд»–ж №жҚ®иҮӘе·ұеӨҡе№ҙжҪңеҝғз ”з©¶жүҖеҫ—еҮәзҡ„зӢ¬еҲ°и§Ғи§ЈпјҢеҜ№е”җе®Ӣд»ҘеүҚжңӘжңүи—Ҹж–Үеӯ—и®°иҪҪзҡ„и—Ҹж—ҸеҺҶеҸІдҪңеҮәдәҶиҫғдёәиҜҰз»Ҷзҡ„и®әиҝ°пјҢиҝҷжҳҜеҚҒеҲҶйҡҫиғҪеҸҜиҙөзҡ„гҖӮжңүдәәз§°иӘүжӯӨд№Ұ“жҳҜдёҖйғЁзӢ¬е…·зү№зӮ№пјҢеЎ«иЎҘз©әзјәзҡ„‘и—Ҹж—ҸеҸІ’з ”з©¶дё“и‘—пјҢиҜҙе®ғж—ўи®әиҜҒдәҶе®үеӨҡең°еҢәи—Ҹж—ҸзӨҫдјҡеҸ‘еұ•еҪўжҖҒпјҢиҝҪиҝ°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зҡ„жәҗжөҒпјҢеҸҲеұ•зҺ°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еҸ‘еұ•зҡ„еҺҶеҸІиҪЁиҝ№пјҢ并д»ҺдёӯжҖ»з»“жҹҗдәӣеҸҜиө„еҖҹйүҙзҡ„з»ҸйӘҢпјҢе…·жңүзҺ°е®һзҡ„еҗҜиҝӘдҪңз”ЁгҖӮ”пјҲи§ҒгҖҠиҘҝеҢ—ж°‘ж—Ҹз ”з©¶гҖӢ1992.2жңҹпјүпјҢд№ҹжҳҜд»–жҷҡе№ҙеҘүзҢ®з»ҷжҲ‘们еҗҺдәәзҡ„дёҖйғЁ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пјҢдё–дәәйҡҫд»Ҙи·Ёи¶Ҡзҡ„и‘—дҪңпјҢеҸ–д№ӢдёҚе°Ҫзҡ„зІҫзҘһиҙўеҜҢе’Ңе®үеӨҡеҸІж•ҷжқҗгҖӮ
з”ұдәҺиҜҘд№Ұжһ„жҖқж–°йў–пјҢеҶ…е®№е……е®һпјҢиө„ж–ҷиҜҰеӨҮпјҢйҳҗиҝ°жҜ”иҫғзі»з»ҹе…ЁйқўпјҢй—®дё–дёҚд№…еҚіеј•иө·зӨҫдјҡйҮҚи§ҶпјҢиў«иҜ„дёә1993йқ’жө·зңҒ第дёүж¬ЎзӨҫдјҡ科еӯҰдјҳз§ҖжҲҗжһңдёҖзӯүеҘ–гҖӮжӯЈжҳҜд»–дёҖз”ҹиҫӣеҠізҡ„еҶҷз…§пјҒз”ұдәҺд»–еңЁеӯҰжңҜдёҠзҡ„иҙЎзҢ®пјҢ1996е№ҙиҺ·еҫ—дәҶдә«еҸ—еӣҪеҠЎйҷўзү№ж®ҠжҙҘиҙҙ专家зҡ„ж®ҠиҚЈгҖӮ
еҪ“и®°иҖ…еҸҠеӯҰз”ҹеҗ‘д»–жҖҖзқҖеҙҮ敬зҡ„еҝғжғ…пјҢиЎЁзӨәз”ұиЎ·зҡ„иөһеҸ№ж—¶пјҢд»–еҚҙж‘Ҷж‘ҶжүӢиҜҙпјҡ“дёҚдёҚпјҢиҝҷе“ӘиғҪе°ұзҹҘи¶ідәҶпјҹиҰҒеҒҡзҡ„дәӢиҝҳеҫҲеӨҡгҖӮеүҚдәӣе№ҙзҷҪзҷҪжөӘиҙ№дәҶйӮЈд№ҲеӨҡеӨ§еҘҪж—¶е…үпјҢиЎҘжҳҜиЎҘдёҚеӣһжқҘдәҶпјҢе”ҜжңүеҠ еҖҚеҠӘеҠӣпјҢж–№и§ЈеҝғеӨҙд№ӢжҶҫе“Әпјҹ”жҲ‘们жғі“дәәдёҖз”ҹжңүдёҖйғЁеҫ—ж„Ҹд№ӢдҪңи¶ізҹЈ”гҖӮиҖҢд»–еңЁйқ’е№ҙж—¶еҮәдәҶдёҖйғЁгҖҠи—ҸжұүеӨ§иҫһе…ёгҖӢпјҢдёӯе№ҙеҸ‘зҺ°зј–иҜ‘дәҶгҖҠе®үеӨҡж”ҝж•ҷеҸІгҖӢпјҢжҷҡе№ҙеҸҲеҮәдәҶдёҖйғЁгҖҠ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еҸІз•ҘгҖӢпјҢйғҪжҳҜз»Ҹе…ёжҖ§зҡ„дј дё–д№ӢдҪңпјҢеҸҜиҜҙжӯӨз”ҹж— жҶҫдәҶгҖӮеҸҜжҳҜд»–иҝҳжҳҜжІЎжңүжҮҲжҖ пјҢйӮЈж—¶еҪ“жңүи®°иҖ…й—®д»–е°ҡжңүдҪ•жү“з®—ж—¶пјҢд»–иҜҙпјҢжӯЈеңЁжҗңйӣҶж•ҙзҗҶжңүе…іиө„ж–ҷпјҢеҮҶеӨҮеҶҷдёҖйғЁи®°иҝ°е®—е–Җе·ҙд»ҘеҗҺи—ҸеӯҰз•Ңжі°ж–—пјҢжңүе№ёзҷ»дёҠ“й»„йҮ‘е®қеә§”зҡ„дҪӣеӯҰ家пјҲз”ҳдё№иөӨе·ҙпјүз”ҹе№ідәӢиҝ№зҡ„и‘—дҪңпјҢеӨ§йғЁеҲҶиө„ж–ҷе·Із»ҸеңЁжүӢгҖҒ并з»ҸеҠ е·Ҙж¶ҰиүІпјҢдёҚд№…еҚіеҸҜи„ұзЁҝйқўдё–гҖӮеӢҝе®№зҪ®з–‘пјҢиҝҷеҸҲжҳҜдёҖйғЁеҠӣдҪңпјҢжҳҜд»–жҷҡе№ҙеҜ№и—ҸеӯҰз ”з©¶е·ҘдҪңеҲ’дёҠзҡ„жңҖе®Ңж»Ўзҡ„еҸҘеҸ·гҖӮзңҹжҳҜ“ж»Ўзӣ®йқ’еұұеӨ•з…§жҳҺ”пјҢеӯҰж— жӯўеўғпјҢ笔иҖ•дёҚиҫҚе•ҠпјҒ
еңЁжҲ‘з»“жқҹиҝҷзҜҮжҖқеҝөиҝҷдҪҚд»ҺеҺҶеҸІй•ҝжІійҮҢиө°жқҘзҡ„е…Ҳй©ұиҖ…пјҢзңӢеҲ°д»–дёәжҲ‘们е®үеӨҡи—Ҹж—ҸеҸІ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дёәеҚ“д»“и—Ҹж—ҸеҸІз”Ёжө“еўЁйҮҚеҪ©зҡ„дёҖйЎөеЎ«иЎҘз©әзҷҪзҡ„ж–Үз« ж—¶пјҢй»ҳй»ҳеҗҹиҜө“еӯҰжө·ж— иҫ№и·Ҝжј«жј«пјҢе‘•еҝғжІҘиЎҖдёәдәәиҙӨгҖӮйӣ„еҝғдёҚе·ІеҲӣж–°дёҡпјҢжҰңж ·ж— еЈ°дәәдәәзҫЎгҖӮ”жҳҜзҡ„пјҢд»–иҷҪ然зҰ»ејҖжҲ‘们已з»ҸдәҢеҚҒе№ҙдәҶпјҢдҪҶд»–зҡ„зІҫзҘһе“Ғеҫ·еғҸжәҗжәҗжҡ–жөҒпјҢж°ёиҝңжөҒж·ҢеңЁжҲ‘们зҡ„еҝғз”°гҖӮ
жң¬ж–ҮеҲҠеҸ‘дәҺйқ’жө·и—Ҹж—Ҹз ”з©¶дјҡдјҡеҲҠгҖҠйқ’жө·и—Ҹж—ҸгҖӢ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