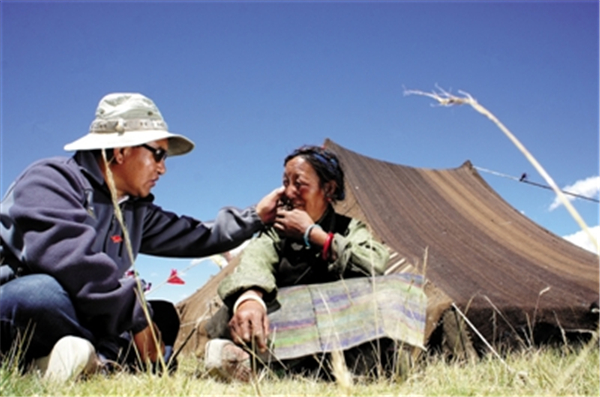5月14日早晨8点整,记者意外地拨通了定居成都的作家阿来的电话。
电话那边,阿来语气一如既往不紧不慢,在45分钟的电话采访快要结束时,他才流露出了不安情绪,很显然,他正在努力克服发自内心的焦虑:“我一个妹妹做客运工作,跑马尔康到成都这条线。12日下午她乘班车离开马尔康,地震发生时车应该开了两百多公里,正好在汶川一带,直到现在都没有联系上她。”
阿来的越野车已经加满了油,他打算,一旦条件允许就驱车赶往灾区,一是为了寻找妹妹,二是看看能为灾民做点什么。阿来的家在成都,但他的故乡在阿坝州,在重灾区汶川县他有不少亲朋好友——
没有急着逃下楼
12日下午,我坐在家里写作。突然间地板动了起来,人猛地晃了一下。我下意识地扶住桌子站起来,可是震得太厉害,根本就迈不开步,我只好又坐了下来。当时我就意识到,地震了。
我硬着头皮坐在椅子上,等震动过去,可震动一直在持续,地板、窗户、床、桌子、椅子都跳动,玻璃杯子撞在一起,噼里啪啦响成一团。我家住在14层,高层房子摇晃的幅度很大,好像马上就要倒了一样。我边强忍地震边想,这下可能要完蛋了。但毫不夸张地说,我没有害怕,我只是很冷静地觉得,这次可能真完了。
震动终于停息下来,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抓起电话,试图向相关政府部门了解情况。拨了几个电话,就是打不通。电话打不通,我就上网查询政府网站,具体查了哪些网站我记不清楚了,总之是能找到的政府网站就上,无论是四川省的还是成都市的。打电话、上网折腾了五六分钟,尚在四川大学读研究生的儿子喊我一起下楼,我们就一起下楼了。下楼时,我用手机给我在马尔康工作的爱人打电话,本意是想通报成都地震、父子平安,以免她听到地震的消息之后着急。还是打不通。当时我以为只是成都打不出去,没想过是那边接不到。这时我隐隐有了一种无助的感觉。终于到了底层,我看到门厅过道全是拖鞋,看来很多人都是慌乱中逃出家门的。
原以为自己就是灾民
我家所在的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反应相当快。他们派保安挨家挨户把人请到楼下的小区公园里,每个楼门口都派人把守,尽量阻止住户回家。非回去不可的,保安都陪着上去。到了公园我开始琢磨,地震是肯定的了,但成都是震中吗?如果不是,震中在哪里呢?我马上就想到了阿坝州,因为1970年代松潘地震时我的家乡震感强烈,我也算是亲身经历过那场地震。再则我还在资料上看到过,1930年代阿坝一带也曾发生过地震。
这么一想我开始不安起来,我的亲人几乎都在阿坝州,他们现在还好吗?不过聚到小区公园里的住户们普遍觉得这场地震就发生在成都,自己就是受灾者。所有人都举着手机在公园里焦急地转悠,但只是说呼语“喂喂”,因为电话根本打不出去。我也是其中之一,我拨了阿坝州每个亲人的电话,越拨越失望。大家开始交流,猜想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成都身上,其中夹杂着一些传言,比如成都市区哪里的楼倒了,人死了之类。不过说者并非信誓旦旦,听者也是姑妄听之。我跟儿子说,成都未必是震中,真正的震中百分之八十在阿坝州一带。
信息流完全断裂,大家都在等待着来自权威部门的消息。地震后的两三个小时,我们做着徒劳的努力,惟一有效的努力就是等待。
故园才是重灾区
我第一次收到确实的消息,是一位匆匆赶回家里的素不相识的住户说的。他说地震发生后他赶紧打车回家,在车上他听广播说,震中在阿坝州汶川县。
紧接着,我收到了北京一位朋友的短信,他说北京地震了,他知道四川阿坝州也地震了,他给我电话打不通,就发短信问我平安。
这两个消息下来,我认定了,震中就在阿坝州。
这样一来,我才发现自己不算受灾者,亲人们的状况才堪忧虑。我一分钟都等不了了,我跟保安说,我的亲人几乎全在阿坝州,我必须得知道他们的情况,手机不通,我要回家用座机试试。
保安允许我回家,我上楼时还有余震,顾不了那么多了,我还是坐电梯上到14层,回到家里。座机还是打不通。我的电脑没关,还在网上挂着呢,我就查询阿坝州政府网站,网页没有显示。
情急之下我打开了电视。没想到电视反应还挺快的,已经开始直播了,接着我又在电视上看到了成都市长的公开讲话。回到小区公园我继续打电话,晚上9点,我终于打通了马尔康的电话,和爱人、两个妹妹都联系上了,他们都安然无恙。只是另一个妹妹出车,大家都联系不上她,我们约好,谁先联系到她就转告大家。
昨天(13日)我跟住在乡下的父母和弟弟也通话了,他们也都没事。
人们比往日懂事
关于这次地震,我只能就我个人的情况发言,就我居住的小区情况发言,别的地方我没有调查,不好说太多。
我们小区的表现让我感到温暖。平日里,大家也许不懂礼让,拥挤喧哗,争先恐后。而这次地震,大家反倒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温情和公德心。以往大家分别住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里,邻里老死不相往来。这次所有人都聚到了小公园里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还有不少坐着轮椅的老人和常年卧病在家的病人,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秩序井然,陌生人之间互相关爱,相互照顾。
大家打招呼,开玩笑,我想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,很多陌生人都会成为朋友。
我们小区整体精神状态比较轻松。社会上,以我有限的观察,我觉得和我们小区情况差不多,至少我没有见到任何乱成一团、失魂落魄的景象。昨天(13日)早上9点,我要去趟单位,就在街上走了一段时间——现在私家车尽量不要上路,以减少交通堵塞。这一路走过去,我最大的感觉是——成都没有休克,生活还在继续,人们比往日更懂事了。
现在,政府和个人在公园里搭了很多帐篷,一家一家地在帐篷里过夜。所有的车里也都住着人。我儿子睡在帐篷里,我睡在车里。我很习惯露宿街头,年轻时我带着睡袋在阿坝的草原上游历,走到哪睡到哪。不过现在下雨,确实挺麻烦。地震那天(12日)晚上没下雨,昨天(13日)中午之后开始下雨,半夜下得还挺大。
物资方面,没有匮乏。我家所在的小区有几千人,两个小超市的商品依然满满的。“囤积”这个词好像用不上,我看到的购物最多的人是买了一箱方便面。我和我儿子只买了几瓶水,几卷饼干。
四川性格,尤其是成都性格似乎更浓郁了。在最没有选择的时候,人们仍然在寻找最安逸的生活方式。
我没看到大面积的愁眉苦脸。相反,有人扎堆喝啤酒,有人喝茶,“摆龙门阵”(闲聊)。打麻将的倒是没见到,不过有不少人扎堆打扑克。还有一些平时难得见面的朋友这次终于聚到了一起,交流交流感情。
昨天黄昏我开车去了一趟郊区的三圣乡。那里的“农家乐”很发达。到了那一看,客流量比节假日还多,人挤得要命。市里的人们是冲着低矮的房屋、空旷的庭院去的,那最适合躲避地震,不过也不可否认,农家小炒和田园风光也是一个诱因。
客人太多了,有的农户临时开起了“农家乐”,家家爆满。老板挺得意地跟我说:“喝茶?等位子吧!”
自古以来“天府之国,水旱从人”,突然间没办法安逸了,大家都有了切身体会,这个心理冲击肯定会在人们心中悄悄潜伏下来。
义务献血站点,每个点都排起了长队。这些献血的人自己的生活还没有恢复正常,有的人家里还没电,或者没水,没气。现在街头上很难打到出租车,我打了一次,那位司机告诉我,他的很多同行都主动开车去灾区义务救灾去了。街头的私家车也少了,很多车主自觉地不上路,以免影响交通。到目前为止,我还没有遇到遇难者家属,但肯定有。从新闻中我了解到的受灾地区和死难人数,我估计我的一些朋友已经不在了,可能还不止一位两位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,接受即将到来的沉痛的现实。
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也许很不讲究,但危急时刻却显示出一种内在的顽强和仁爱风范,并非如某些文化决定论者妄断的那样不堪。开个玩笑——我们会过坏日子,不会过好日子吧。也许是因为刚脱贫吧。
到目前为止,我感觉可怕的是现代化的脆弱,一是交通,二是通讯。现代生活对人的改变太大了,以前的人遇到类似情况首先做什么呢?现在的人首先是获得信息,手机不通人就束手无策,近乎于丧失决策能力和行为能力了。
我亲身经历过松潘地震,当时家在农村,能感觉到震动,但离震中较远,大家没有惊慌,只是有一点不安,那种乐观也可以说是带有宿命论色彩的乐观。唐山大地震离我们家乡虽然遥远,但却是举世罕见的浩劫,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那个灾难。
在小说《尘埃落定》中我写过地震——有一年发生了地震,麦其土司家的罂粟却获得了大丰收。不过我在《尘埃落定》里写地震不是由于我对地震的印象深刻,只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讲,我觉得就应该那么写,如果非要从中寻找“微言大义”恐怕不合适。
眼下各个单位都在想着为灾区做点什么。我是省青联副主席,我们也正在商量我们的专业能为灾区做什么。我个人最担心的就是妹妹,我已经准备好了,随时准备出发去找她。